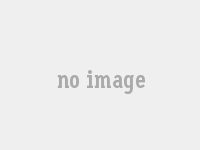男生成长的表现(小孩的成长故事怎么写男孩的成长,就是一次次死里逃生)
偶尔刷短视频,听到一句话“男孩的成长就是一次次死里逃生”,觉得很有道理。

我这辈子,有几次与死亡狭路相逢,甚至擦肩而过的经历。
第一次是3岁时,患麻疹转肺炎,在医院住了十多天。最惨烈的时候,高烧三天不退。水米不进,只能用棉签面水浸嘴唇。同病室的小孩,时不时就被送去太平间,我的父亲抱着我,哭成泪人。在母亲记忆里。父亲只哭过两回,另一回,是我13岁那年拿着双刀与他对峙。事后向他认错道歉的时候。
第二次是5岁那年,在四川电视台工地上,我和一帮同样没人带的“建二代”一起,在工地上蹿下跳,像森林里嬉戏的小猴,完全不知道危险的存在。不知身边一个小小的物件,无论是一枚铁钉还是一根钢筋或飞石,都会像林中的蟒蛇或鳄鱼。可以轻易要了我们的小命。
那是个寂静的中午,大家都睡了,我无聊地来到洗灰池边,洗灰池深几米,全装着经过沉淀之后的细石灰,池面上积着尘土,投一块石头下去,就绽开一朵白花,十分神奇。这让我有一种想把自己扔进去的冲动,看看能溅出什么来。于是,我跳了进去,洗灰池表面像天上笃实的云海,看上去似乎可以站人,但事实上却是空的,人一踩上去,立即下陷,如沼泽一般。比沼泽更恐怖的是,那下面是有强大腐蚀性的石灰泥····
我一路下滑,完全失去意识。温热的石灰膏,如一张巨嘴。把我吞咽下去......
就在这时,一双大手捏住了我的后脖领,将我拎了起来。那是父亲的同事王老虎,他平时都在附近的木工棚睡午觉。那天中午,正熟睡的他被“咚”的一声惊醒了——那是我往石灰池里扔石头炸“花”的声音,他来制止我的破坏,不想却教了我一命。
再一次,是在姨妈插队的乡下,也是一个中午。有人说,小男孩的成长,就是一个又一个死里逃生的过程,而这些“死”,有很大部分是自己“作”出来的。那天,我又“作”起来。
那本是一个并不太热的中午,而我想游泳,村里的小伙伴。要么要干家务,要么觉得天凉不想游。于是,我这个城里来的学龄前儿重闲极无聊地来到水边,指望能遇到和我一样闲得皮痒的人。

我脱了衣裤,沿着河滩斜面往水里走去。平时,有大孩子们一道,他们个子高,能为我丈量水的深度,为我设定一个界限,水漫到他们胸的地方,就是我的禁区。
今天,禁区没有了。我愉悦地体验着突破禁区的快感,轻轻一蹦,水深一点,轻轻地再一蹦,又深一点,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我感受着失去重力的快乐,像太空人在月球上那样,一步步蹦向深渊......说深渊有些夸张,水的最深处只有一米多,淹不过成年人,但淹我绰绰有余。我跳着跳着,脚下突然就空了,而再努力探到底时,水没过了头顶,世界瞬间变得稀里哗啦,河边的竹林、树和甘蔗,疯一般的惊叫,我努力跳着,但每跳一次,水就更深一些。直至一口水呛进嘴里,眼前一片漆黑……
再次醒来时,我趴在一个热乎乎毛茸茸的东西上面,仔细看,是头大水牛。牵牛的是村里养牛的牛旺叔,我在村里最不喜欢的人。他时常揭穿我骗小朋友们的谎言,比如,我说我爸参加过八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什么的,他都会拆穿我。其实别的孩子未必不知道我在撒谎骗他们,但他们却当故事来听,也还算新鲜好玩。
那天,牛旺叔进城买牛,在城里撞见卖瘟猪肉的,贪嘴吃了几两,半路肚子里就滚了雷,跑到甘蔗田里解决,结果意外救了我一命。
这些年跑新闻,我也算是见过生死的,无论是地震灾区还是车祸现场,或者出事的矿洞和悲伤的ICU病房,我见过无数的身体在生命离开之后变得苍白僵硬的样子。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受邀为一家报纸写社论,其中有一句“经此大难,有人会活得更庄重,有人会活得更放纵”。这是在地震灾区采访多日,见到无数劫后余生的人的真实反应之后,油然而生的想法。
对死亡的认知,可以改变人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以我身边一些熟人为例,当大家开始意识到,生命是那么脆弱和偶然的时候,舍不得花的钱,舍得了;放不下的感情,放下了;丢不开的争执,丢开了;想不通的事,想通了。生死面前,一切都是小事。这与其说是通透,倒莫如说是一种服气。
当然,死亡于人,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终结,一种时限。许多东西,因为有了这种限制,而变得更加值得珍惜。所有“得到”,会因为终将“失去”而显得更加珍贵。生,因为死的存在,而显得更加灿烂和值得珍惜。

有人说,人其实每天都在经历生死,我们身上的细胞,像忒修斯之船时常都在更换船板一般,每天都在新陈代谢。而每天从纷繁扰攘的世界经过,有多少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危险,与我们擦肩而过。每一次闭眼睡去,都可能是一次安详的离去;每一次睁眼醒来,都是一次幸运和祝福。在眼前这片金色的朝阳里,回想自己经历的那些侥幸,我感到万分幸运——如果从3岁那次算起,我已经被祝福了50年,这50年尝到的所有酸甜苦辣麻,以及笑过哭过愉悦过痛苦过的所有记忆,都是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