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起源与目的的作者(画一画自己的成长故事《的》的作者朱奈达:不被固定观念抓住,画难以被归类的绘本新京报2023-12-25 16:03新京报2023-12-25 16:03)
有一位创作者,他的第二本绘本《的》刚被引进,就用无穷的想象和思辨的乐趣捉住了读者的心,他就是日本绘本创作者朱奈达。不仅读者会感叹朱奈达是“何方神圣”,在吉竹伸介眼里,朱奈达也极其神秘,是“被另一个世界的怪物选中的传真机,通过他的手把另一个世界打印到了我们的世界里”。朱奈达的绘画风格细腻明亮,故事的设计又极具超越性。许多读者会误认为他是女性创作者,甚至他自己都打趣道:“还有人以为我是个金发碧眼的女作家!” 朱奈达。这位看似神秘且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其实有其质朴、极具行动力的一面。为了打破绘本的固定观念,朱奈达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探索着不同的核心形式;为了确保创作的自由,他自己开书店和画廊,出版、展示自己的作品;而当他的作品已经获得成功,再无出版和展览方面的困扰后,朱奈达果断地关闭了书店,投身新的未来。在早年玩乐队时期,朱奈达的理念就是:“不要被固定观念抓住,不区分特定的类别,让流行、摇滚、打击乐与电子音乐交织。”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奈达是如何用行动在绘本领域践行他这一核心理念,不断突破,并且将肆无忌惮地去想象的力量交到每一个读者的手中。本文也是新京报小童书系列专栏“写童书的人”中的一篇。在这个专栏中,我们尽量全面、准确地讲述创作者们的人生故事,尝试探究那些极具原创性的童书,到底是如何从作者的性格、生命体验中生长出来的。而且我们相信:看见不同的人生,或许能让我们的心中有更多的活法,不至于被当下的诸多定义、规则束缚。该专栏即将结集成书,敬请期待。画一本难以被归类、没有标准答案的绘本在出版绘本之前,朱奈达已经作为插画师工作多年,出过十几本画集,是小有名气的画家。2016年,福音馆书店正在策划一本幻想性很强的儿童文学作品《从背中町走来》,故事的舞台背中町坐落在年老海王的背部,讨论到插图与封面设计时,编辑和作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奈达——那个给三越百货画广告的画家,很喜欢在人、物之上建造另一层人、物。朱奈达觉得物件也好,建筑物也好,都是灌满使用者、居住者记忆的容器,而记忆又能以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的形式呈现,多么适配福音馆正在推进的这本童话集。
朱奈达。这位看似神秘且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其实有其质朴、极具行动力的一面。为了打破绘本的固定观念,朱奈达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探索着不同的核心形式;为了确保创作的自由,他自己开书店和画廊,出版、展示自己的作品;而当他的作品已经获得成功,再无出版和展览方面的困扰后,朱奈达果断地关闭了书店,投身新的未来。在早年玩乐队时期,朱奈达的理念就是:“不要被固定观念抓住,不区分特定的类别,让流行、摇滚、打击乐与电子音乐交织。”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奈达是如何用行动在绘本领域践行他这一核心理念,不断突破,并且将肆无忌惮地去想象的力量交到每一个读者的手中。本文也是新京报小童书系列专栏“写童书的人”中的一篇。在这个专栏中,我们尽量全面、准确地讲述创作者们的人生故事,尝试探究那些极具原创性的童书,到底是如何从作者的性格、生命体验中生长出来的。而且我们相信:看见不同的人生,或许能让我们的心中有更多的活法,不至于被当下的诸多定义、规则束缚。该专栏即将结集成书,敬请期待。画一本难以被归类、没有标准答案的绘本在出版绘本之前,朱奈达已经作为插画师工作多年,出过十几本画集,是小有名气的画家。2016年,福音馆书店正在策划一本幻想性很强的儿童文学作品《从背中町走来》,故事的舞台背中町坐落在年老海王的背部,讨论到插图与封面设计时,编辑和作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奈达——那个给三越百货画广告的画家,很喜欢在人、物之上建造另一层人、物。朱奈达觉得物件也好,建筑物也好,都是灌满使用者、居住者记忆的容器,而记忆又能以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的形式呈现,多么适配福音馆正在推进的这本童话集。 朱奈达给三越百货画的广告画。编辑找到朱奈达,插画合作谈得很愉快,还有意外收获,聊天中朱奈达说起自己曾想画这样一本绘本:表面上没有故事,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书中自由生长,各不相同的人在书中自由居住,无论从哪里开始读、无论怎么读,每次读都有新发现。朱奈达的构想很快有了实体,也就是他的第一本绘本《路》。这本绘本没有文字,男孩从左端出发,女孩从右端启程,翻过一页又一页主题不同、道路近似迷宫的城市……看起来像迷宫游戏书,仔细读却发现它也不算迷宫,不管你怎么走,总能通过这座城市,走去下一个城市。而每一条街道角落里,有许多活生生的,似乎怀揣着自己故事的居民。
朱奈达给三越百货画的广告画。编辑找到朱奈达,插画合作谈得很愉快,还有意外收获,聊天中朱奈达说起自己曾想画这样一本绘本:表面上没有故事,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书中自由生长,各不相同的人在书中自由居住,无论从哪里开始读、无论怎么读,每次读都有新发现。朱奈达的构想很快有了实体,也就是他的第一本绘本《路》。这本绘本没有文字,男孩从左端出发,女孩从右端启程,翻过一页又一页主题不同、道路近似迷宫的城市……看起来像迷宫游戏书,仔细读却发现它也不算迷宫,不管你怎么走,总能通过这座城市,走去下一个城市。而每一条街道角落里,有许多活生生的,似乎怀揣着自己故事的居民。 《路》,作者: [日] 朱奈达,译者: 浪花朵朵,出品方: 后浪,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9月。创意足够奇怪,又足够有趣,值得一遍又一遍地品读,它打动了编辑,让编辑也热血、“任性”了起来——据编辑说,福音馆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绘本,选题会通过得很艰难,对接的书店也不看好,店员们纷纷发愁:都不知道怎么卖这本书,到底是艺术书还是绘本,是给成人看的还是给孩子看的呢?这个困扰出版方的问题,从未困扰过朱奈达,或者说,早在1997年,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因如此,朱奈达才会在20年后“想要画一本绘本”。1997年,朱奈达还是正在备考美术学校的高三生,他在常去的画室书架上翻到了一本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展图册,可爱的、恐怖的、尖锐的……作品风格的多样程度令他大吃一惊,也让他对于绘本“就是逗逗小孩的”这个刻板印象“啪”地一下破裂了。绘本为什么非得要划分得一清二楚呢?在唱片店里朋克音乐的架子上翻到摇滚音乐,不也一样听得开心吗?不仅不受分类问题的困扰,朱奈达反而希望自己的绘本能变得分类暧昧。年少时喜欢探索未知的道路的朱奈达,确信孩子们会享受在《路》中自由探索的乐趣。他也希望成年人能够借助阅读《路》,重启自己的想象之力。想象主人公和图画中的居民有何互动,那两个人是恋人还是朋友,两位主人公会命中注定地相遇,还是会擦肩而过……这本书没有任何“标准答案”。
《路》,作者: [日] 朱奈达,译者: 浪花朵朵,出品方: 后浪,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9月。创意足够奇怪,又足够有趣,值得一遍又一遍地品读,它打动了编辑,让编辑也热血、“任性”了起来——据编辑说,福音馆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绘本,选题会通过得很艰难,对接的书店也不看好,店员们纷纷发愁:都不知道怎么卖这本书,到底是艺术书还是绘本,是给成人看的还是给孩子看的呢?这个困扰出版方的问题,从未困扰过朱奈达,或者说,早在1997年,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因如此,朱奈达才会在20年后“想要画一本绘本”。1997年,朱奈达还是正在备考美术学校的高三生,他在常去的画室书架上翻到了一本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展图册,可爱的、恐怖的、尖锐的……作品风格的多样程度令他大吃一惊,也让他对于绘本“就是逗逗小孩的”这个刻板印象“啪”地一下破裂了。绘本为什么非得要划分得一清二楚呢?在唱片店里朋克音乐的架子上翻到摇滚音乐,不也一样听得开心吗?不仅不受分类问题的困扰,朱奈达反而希望自己的绘本能变得分类暧昧。年少时喜欢探索未知的道路的朱奈达,确信孩子们会享受在《路》中自由探索的乐趣。他也希望成年人能够借助阅读《路》,重启自己的想象之力。想象主人公和图画中的居民有何互动,那两个人是恋人还是朋友,两位主人公会命中注定地相遇,还是会擦肩而过……这本书没有任何“标准答案”。 《路》内文图。《路》里不使用文字,正是为了不让文字限制读者想象的自由度。朱奈达甚至期盼读者别把绘本当绘本,而是将它视作游戏道具,自己,或者是和亲人朋友一起,用想象创造自己版本的奇妙且奇异的世界。“我把想象的喜悦像接力棒一样交到读者手中,等某一天读者把这根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个人,这本绘本才算真正意义上完成!”在朱奈达看来,读者借由自己的绘本创造自己的世界,才是绘本得以成立的证明。这本分类暧昧的绘本在编辑的信任下,得以在2018年成功出版,而且并没有像书店店员预测的那么难卖。成人读者很喜欢,小读者也是,有一次编辑在书店布置朱奈达的宣传板,听到一个小朋友大老远就在喊“我知道那个人,我知道那个人!”实际上,店员们自己也很喜欢,纷纷写文推荐,《路》因此拿到了由书店店员投票产生的“MOE绘本书店大奖”。向正在成型的普遍想象投出一块石头《路》大获成功后,朱奈达提出一个新的绘本构想,却和此前的“无字绘本”截然相反,其核心是“文字游戏”。有一天,他偶然意识到,“的”是一个神奇的介词,它可以表达“在里面”“在上面”“从属于”等各种关系,无论本身关系多遥远的两样东西,总能借助“的”黏合在一起。朱奈达立刻试验了起来,从“我”开始,想到自己常画的那个红衣女孩,又试图让“的”变得更有魔力,于是,他想到往女孩的口袋里置入一点普通口袋装不下的奇怪东西,比如城堡,又把城堡里的床单变成大海,再到马戏团、森林、图书馆、云端、小鸟时钟、银河尽头、巨人画布、纸飞机公主……
《路》内文图。《路》里不使用文字,正是为了不让文字限制读者想象的自由度。朱奈达甚至期盼读者别把绘本当绘本,而是将它视作游戏道具,自己,或者是和亲人朋友一起,用想象创造自己版本的奇妙且奇异的世界。“我把想象的喜悦像接力棒一样交到读者手中,等某一天读者把这根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个人,这本绘本才算真正意义上完成!”在朱奈达看来,读者借由自己的绘本创造自己的世界,才是绘本得以成立的证明。这本分类暧昧的绘本在编辑的信任下,得以在2018年成功出版,而且并没有像书店店员预测的那么难卖。成人读者很喜欢,小读者也是,有一次编辑在书店布置朱奈达的宣传板,听到一个小朋友大老远就在喊“我知道那个人,我知道那个人!”实际上,店员们自己也很喜欢,纷纷写文推荐,《路》因此拿到了由书店店员投票产生的“MOE绘本书店大奖”。向正在成型的普遍想象投出一块石头《路》大获成功后,朱奈达提出一个新的绘本构想,却和此前的“无字绘本”截然相反,其核心是“文字游戏”。有一天,他偶然意识到,“的”是一个神奇的介词,它可以表达“在里面”“在上面”“从属于”等各种关系,无论本身关系多遥远的两样东西,总能借助“的”黏合在一起。朱奈达立刻试验了起来,从“我”开始,想到自己常画的那个红衣女孩,又试图让“的”变得更有魔力,于是,他想到往女孩的口袋里置入一点普通口袋装不下的奇怪东西,比如城堡,又把城堡里的床单变成大海,再到马戏团、森林、图书馆、云端、小鸟时钟、银河尽头、巨人画布、纸飞机公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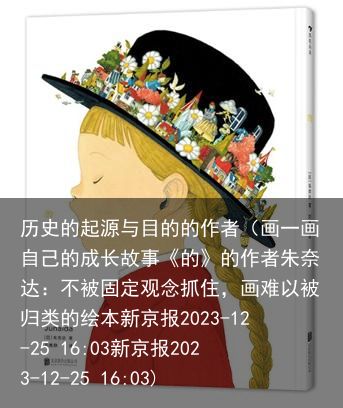 《的》,作者: [日] 朱奈达,译者: 刘雅静,出品方: 后浪,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时间: 2023年10月。从图像上归类,《的》又是一本变焦绘本。这类绘本把动态的摄像镜头艺术和静态的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通过镜头拉近、拉远讲故事,从一开始就是绘本世界里的先锋派,也诞生了不少经典作品,比如《变焦》《海底的秘密》《小红书》。而朱奈达没有遵循镜头有规律变焦这一惯例,《的》的场景时而现实,时而虚幻,空间时而磅礴,时而袖珍,入口也没有那么清晰可见,有时隐藏在未翻盖的衣兜里,以至于读者永远猜不透这一页最后一个“的”字,会在下一页连接什么样的东西,可等翻到下一页,又觉得和上一页关系如此紧密。《的》像是一部奇幻动画长片,钻进一个小洞,结果来到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恍若一层层变幻莫测的梦境,嵌套的方式没什么道理。当你以为这梦境要没完没了的时候,它又巧妙地落幕在绿衣服花冠帽子女孩的口袋里的“我”,让一直坠落又好像一直上升的读者,轻盈地脚落实地。(不过,最后的“我”也可以紧接封面上的“的”,从而变成无始无终的巡游——这是装帧设计师最终决定让书名字号和内文字号大小差不多的原因。)朱奈达的创意挑战还在继续,2020年,他在第三本绘本《怪物园》里有意识地挑战人们的刻板观念。怪物不小心闯进了城市,在大街上漫游前行,人类小孩只能躲在家里,用一个大纸箱子玩想象游戏。
《的》,作者: [日] 朱奈达,译者: 刘雅静,出品方: 后浪,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时间: 2023年10月。从图像上归类,《的》又是一本变焦绘本。这类绘本把动态的摄像镜头艺术和静态的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通过镜头拉近、拉远讲故事,从一开始就是绘本世界里的先锋派,也诞生了不少经典作品,比如《变焦》《海底的秘密》《小红书》。而朱奈达没有遵循镜头有规律变焦这一惯例,《的》的场景时而现实,时而虚幻,空间时而磅礴,时而袖珍,入口也没有那么清晰可见,有时隐藏在未翻盖的衣兜里,以至于读者永远猜不透这一页最后一个“的”字,会在下一页连接什么样的东西,可等翻到下一页,又觉得和上一页关系如此紧密。《的》像是一部奇幻动画长片,钻进一个小洞,结果来到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恍若一层层变幻莫测的梦境,嵌套的方式没什么道理。当你以为这梦境要没完没了的时候,它又巧妙地落幕在绿衣服花冠帽子女孩的口袋里的“我”,让一直坠落又好像一直上升的读者,轻盈地脚落实地。(不过,最后的“我”也可以紧接封面上的“的”,从而变成无始无终的巡游——这是装帧设计师最终决定让书名字号和内文字号大小差不多的原因。)朱奈达的创意挑战还在继续,2020年,他在第三本绘本《怪物园》里有意识地挑战人们的刻板观念。怪物不小心闯进了城市,在大街上漫游前行,人类小孩只能躲在家里,用一个大纸箱子玩想象游戏。 《怪物园》原版封面。或许会有读者想起经典绘本《野兽国》,马克斯在现实世界里和妈妈吵了架,于是通过想象进入了野兽们的世界。然而在朱奈达笔下,怪物们出没的灰暗城市是现实世界,孩子们浪游的明亮场所才是想象世界。“这种意想不到、奇怪的感觉,正是我要创造的。”虽然题材、形式、画风各异,《的》与《怪物园》却在某一点上延续了《路》的路线。当年朱奈达坚持绘本无需区分“给大人看”还是“给孩子看”,想把绘本变成所有人都能不受界限束缚而享受的东西。而此刻,朱奈达说,“现在的绘本,有一种作用是向正在成为普遍想象的东西,投出一块石头,尝试去做改变。”为了创作的自由,自己开书店和画廊在2004年的小展览中,朱奈达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根据感觉创作的人。”无论是画画、音乐、与人接触,都在创造感觉,当他在桌上摆好纸和笔,会先闭上眼睛,让感觉流动,变成波浪,直到冲撞成图像。这种凭借感觉创作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前两年的对谈中,朱奈达再次提到自己创作的时候,日常中闭锁着的纯然感性的心门会完全打开,在这种状态下,除了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画画,全身心投入其中。从具体的生活里汲取抽象感觉,再把它们塑成图像的方式,令朱奈达无意中创作了几类固定意象:门与钥匙、马戏团、音乐、书……这些物件不仅承载着作品中人物的记忆,也凝缩着朱奈达自己的记忆。比如,《的》中在森林图书馆的书架上翻看图书的刺猬,便会让熟悉朱奈达的读者想起他的另一个身份——京都鸭川河畔“刺猬书店&画廊”(Hedgehog Books&Gallery)的店长。
《怪物园》原版封面。或许会有读者想起经典绘本《野兽国》,马克斯在现实世界里和妈妈吵了架,于是通过想象进入了野兽们的世界。然而在朱奈达笔下,怪物们出没的灰暗城市是现实世界,孩子们浪游的明亮场所才是想象世界。“这种意想不到、奇怪的感觉,正是我要创造的。”虽然题材、形式、画风各异,《的》与《怪物园》却在某一点上延续了《路》的路线。当年朱奈达坚持绘本无需区分“给大人看”还是“给孩子看”,想把绘本变成所有人都能不受界限束缚而享受的东西。而此刻,朱奈达说,“现在的绘本,有一种作用是向正在成为普遍想象的东西,投出一块石头,尝试去做改变。”为了创作的自由,自己开书店和画廊在2004年的小展览中,朱奈达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根据感觉创作的人。”无论是画画、音乐、与人接触,都在创造感觉,当他在桌上摆好纸和笔,会先闭上眼睛,让感觉流动,变成波浪,直到冲撞成图像。这种凭借感觉创作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前两年的对谈中,朱奈达再次提到自己创作的时候,日常中闭锁着的纯然感性的心门会完全打开,在这种状态下,除了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画画,全身心投入其中。从具体的生活里汲取抽象感觉,再把它们塑成图像的方式,令朱奈达无意中创作了几类固定意象:门与钥匙、马戏团、音乐、书……这些物件不仅承载着作品中人物的记忆,也凝缩着朱奈达自己的记忆。比如,《的》中在森林图书馆的书架上翻看图书的刺猬,便会让熟悉朱奈达的读者想起他的另一个身份——京都鸭川河畔“刺猬书店&画廊”(Hedgehog Books&Gallery)的店长。 《的》内文图照片。2010年6月,朱奈达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刺猬书店开业的消息,他说:“今后我会以朱奈达(Junaida)为名,以刺猬书店(Hedgehog)为据点,尝试做各种各样快乐的事情。”——这是朱奈达走出迷茫期的起点。上大学时的朱奈达无疑是迷茫的,明明喜欢画画,对技艺也有自信,却偏偏无心画画,反倒是全身心玩起了乐队。在他看来,那时候的作品回顾起来缺乏灵魂,绝对不会示众。2001年从京都精华大学漫画学部毕业后,朱奈达一边当自由插画师,给包括时尚杂志、警察局在内的各种机构画插画,一边继续玩乐队。2004年是朱奈达职业生涯上的第一个变化期,他参加了艺人事务所“AMUSE”主办的艺术奖,并在之后进入“AMUSE”事务所当专职插画师。
《的》内文图照片。2010年6月,朱奈达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刺猬书店开业的消息,他说:“今后我会以朱奈达(Junaida)为名,以刺猬书店(Hedgehog)为据点,尝试做各种各样快乐的事情。”——这是朱奈达走出迷茫期的起点。上大学时的朱奈达无疑是迷茫的,明明喜欢画画,对技艺也有自信,却偏偏无心画画,反倒是全身心玩起了乐队。在他看来,那时候的作品回顾起来缺乏灵魂,绝对不会示众。2001年从京都精华大学漫画学部毕业后,朱奈达一边当自由插画师,给包括时尚杂志、警察局在内的各种机构画插画,一边继续玩乐队。2004年是朱奈达职业生涯上的第一个变化期,他参加了艺人事务所“AMUSE”主办的艺术奖,并在之后进入“AMUSE”事务所当专职插画师。 朱奈达早年为自己乐队画的专辑封面。做专职插画师,就不能在作品里投入太多个人属性,必须以客户需求为准,更何况所在公司又不是专业经营美术经纪的公司。虽然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同伴也都很优秀,朱奈达却无所适从,“并不是说专职插画师职业有问题,我身边优秀的插画师们很擅长应对客户的需求……我渐渐觉得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做插画师,更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画自己的画。”以“感觉”为画笔的画家,很难适应以“需求”为准则的插画工作。刺猬书店是为了把画画和生计拆分开而开业的。书店里售卖各种图书与杂货,本身就是盈利的。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展览空间,有时展陈朱奈达自己的作品,有时则是其他插画师的画。如此一来,如果自己想画的画没地方愿意展陈,那就放在刺猬书店;假如出版社不愿和他一起挑战闻所未闻的创作,也能以刺猬书店的名义出版;如果作品没有好到吸引人购买,也总有人愿意买一张明信片、一个徽章,而这同样是一种认可。几乎可以说,书店就像尖刺,保护着朱奈达创作的自由——而这就像刺猬柔软的肚皮。朱奈达得以用自己舒适的感觉创作法,把自己对于生活感觉的记忆,变形成图像,去表达物件、建筑是装载人们记忆的容器这一想法。沿着这一方向前进,才有了此后引起福音馆编辑关注的三越百货广告画,以及画下《路》《的》《怪物园》的朱奈达。想描绘超越现在的未来,于是再一次出发2021年6月,书店开业11周年之际,朱奈达宣布关闭线下店铺。“‘刺猬’随着我们的成长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我们想要描绘超越这种变化的未来时,作为门店的‘刺猬’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是时候进入下一步了。第10周年时我就有了这种预感。”紧接着的7月,朱奈达出版了一本新绘本《城市小偷》。这是朱奈达创作的绘本中最接近一般故事绘本形态的作品,故事超越了图像与感觉,成为了绘本的主角。山顶上住着一位孤独的巨人,某个晚上,巨人寂寞得没有办法了,便去山脚下的城市偷了一座房子回来。巨人请求这一家人:“从今往后我们就在这里一起生活吧。你们要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无论什么我都会带给你们。”
朱奈达早年为自己乐队画的专辑封面。做专职插画师,就不能在作品里投入太多个人属性,必须以客户需求为准,更何况所在公司又不是专业经营美术经纪的公司。虽然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同伴也都很优秀,朱奈达却无所适从,“并不是说专职插画师职业有问题,我身边优秀的插画师们很擅长应对客户的需求……我渐渐觉得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做插画师,更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画自己的画。”以“感觉”为画笔的画家,很难适应以“需求”为准则的插画工作。刺猬书店是为了把画画和生计拆分开而开业的。书店里售卖各种图书与杂货,本身就是盈利的。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展览空间,有时展陈朱奈达自己的作品,有时则是其他插画师的画。如此一来,如果自己想画的画没地方愿意展陈,那就放在刺猬书店;假如出版社不愿和他一起挑战闻所未闻的创作,也能以刺猬书店的名义出版;如果作品没有好到吸引人购买,也总有人愿意买一张明信片、一个徽章,而这同样是一种认可。几乎可以说,书店就像尖刺,保护着朱奈达创作的自由——而这就像刺猬柔软的肚皮。朱奈达得以用自己舒适的感觉创作法,把自己对于生活感觉的记忆,变形成图像,去表达物件、建筑是装载人们记忆的容器这一想法。沿着这一方向前进,才有了此后引起福音馆编辑关注的三越百货广告画,以及画下《路》《的》《怪物园》的朱奈达。想描绘超越现在的未来,于是再一次出发2021年6月,书店开业11周年之际,朱奈达宣布关闭线下店铺。“‘刺猬’随着我们的成长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我们想要描绘超越这种变化的未来时,作为门店的‘刺猬’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是时候进入下一步了。第10周年时我就有了这种预感。”紧接着的7月,朱奈达出版了一本新绘本《城市小偷》。这是朱奈达创作的绘本中最接近一般故事绘本形态的作品,故事超越了图像与感觉,成为了绘本的主角。山顶上住着一位孤独的巨人,某个晚上,巨人寂寞得没有办法了,便去山脚下的城市偷了一座房子回来。巨人请求这一家人:“从今往后我们就在这里一起生活吧。你们要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无论什么我都会带给你们。” 《城市小偷》原版照片。这家人便让巨人把亲戚们的房子也搬上山,亲戚们又请求巨人把他们的朋友的房子也搬上山,直到几乎整个城市都被搬到了山顶上,大家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然而巨人的寂寞并未消解,他决定独自下山。在山脚下的城市,还有一个男孩和他的房子……朱奈达为这本绘本写了一篇长长的创作手记,因为写下这个故事后,他意识到也许这是个写给儿时自己的故事。朱奈达小时候经常转学,不管身处哪里,都感觉脚下空落落的,好像自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倒也不是没交过朋友,只是感觉不熟悉那片土地,和周围人是不一样的,不属于那里。他对当年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种感受印象深刻,如今,这种感受以蹲坐在城市之间的孤独巨人的形象复现。“我想,这个故事里的巨人会抵达的所在,每个人的想象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当年的我来说,那个所在是音乐。14岁第一次听朋克音乐时,我感觉自己和世界相接的那道门第一次打开了。”但如今看来,朋克音乐不是朱奈达与世界连接的终点,创造了快乐回忆的刺猬书店也不一定是终点。“我们会在和人相遇中找到门钥匙,遇到和自己有共鸣的人或事,就算踏出了第一步。但找到钥匙并不容易,你也可以试着去别的地方,不必停留在哪里,继续往前走就好。”像巨人决定下山,就像《路》的主人公也可以选择擦肩而过,继续自己的探索,就像《的》的无始无终,喜欢打破普遍想象的朱奈达从不满足于停留于某处,他选择继续寻找新的可能性。近两年间,朱奈达在佐仓市立美术馆等大型美术馆举办了个展,并计划全国巡展。他的确正在描绘超越过去的未来。参考资料:1.朱奈达个人官网https://www.junaida.com/2.HOBO×朱奈达专访https://www.1101.com/junaida/2015-06-09.html3.《的》日版出版对谈(祖父江慎×朱奈达)https://www.fukuinkan.co.jp/blog/detail/?id=4494.《城市小偷》作者创作手记https://www.fukuinkan.co.jp/blog/detail/?id=5025.福音馆编辑冈田望专访https://play2020.jp/article/junaida_interview_okada_3/ 撰文/吴回音编辑/王铭博校对/薛京宁举报/反馈
《城市小偷》原版照片。这家人便让巨人把亲戚们的房子也搬上山,亲戚们又请求巨人把他们的朋友的房子也搬上山,直到几乎整个城市都被搬到了山顶上,大家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然而巨人的寂寞并未消解,他决定独自下山。在山脚下的城市,还有一个男孩和他的房子……朱奈达为这本绘本写了一篇长长的创作手记,因为写下这个故事后,他意识到也许这是个写给儿时自己的故事。朱奈达小时候经常转学,不管身处哪里,都感觉脚下空落落的,好像自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倒也不是没交过朋友,只是感觉不熟悉那片土地,和周围人是不一样的,不属于那里。他对当年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种感受印象深刻,如今,这种感受以蹲坐在城市之间的孤独巨人的形象复现。“我想,这个故事里的巨人会抵达的所在,每个人的想象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当年的我来说,那个所在是音乐。14岁第一次听朋克音乐时,我感觉自己和世界相接的那道门第一次打开了。”但如今看来,朋克音乐不是朱奈达与世界连接的终点,创造了快乐回忆的刺猬书店也不一定是终点。“我们会在和人相遇中找到门钥匙,遇到和自己有共鸣的人或事,就算踏出了第一步。但找到钥匙并不容易,你也可以试着去别的地方,不必停留在哪里,继续往前走就好。”像巨人决定下山,就像《路》的主人公也可以选择擦肩而过,继续自己的探索,就像《的》的无始无终,喜欢打破普遍想象的朱奈达从不满足于停留于某处,他选择继续寻找新的可能性。近两年间,朱奈达在佐仓市立美术馆等大型美术馆举办了个展,并计划全国巡展。他的确正在描绘超越过去的未来。参考资料:1.朱奈达个人官网https://www.junaida.com/2.HOBO×朱奈达专访https://www.1101.com/junaida/2015-06-09.html3.《的》日版出版对谈(祖父江慎×朱奈达)https://www.fukuinkan.co.jp/blog/detail/?id=4494.《城市小偷》作者创作手记https://www.fukuinkan.co.jp/blog/detail/?id=5025.福音馆编辑冈田望专访https://play2020.jp/article/junaida_interview_okada_3/ 撰文/吴回音编辑/王铭博校对/薛京宁举报/反馈
 朱奈达。这位看似神秘且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其实有其质朴、极具行动力的一面。为了打破绘本的固定观念,朱奈达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探索着不同的核心形式;为了确保创作的自由,他自己开书店和画廊,出版、展示自己的作品;而当他的作品已经获得成功,再无出版和展览方面的困扰后,朱奈达果断地关闭了书店,投身新的未来。在早年玩乐队时期,朱奈达的理念就是:“不要被固定观念抓住,不区分特定的类别,让流行、摇滚、打击乐与电子音乐交织。”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奈达是如何用行动在绘本领域践行他这一核心理念,不断突破,并且将肆无忌惮地去想象的力量交到每一个读者的手中。本文也是新京报小童书系列专栏“写童书的人”中的一篇。在这个专栏中,我们尽量全面、准确地讲述创作者们的人生故事,尝试探究那些极具原创性的童书,到底是如何从作者的性格、生命体验中生长出来的。而且我们相信:看见不同的人生,或许能让我们的心中有更多的活法,不至于被当下的诸多定义、规则束缚。该专栏即将结集成书,敬请期待。画一本难以被归类、没有标准答案的绘本在出版绘本之前,朱奈达已经作为插画师工作多年,出过十几本画集,是小有名气的画家。2016年,福音馆书店正在策划一本幻想性很强的儿童文学作品《从背中町走来》,故事的舞台背中町坐落在年老海王的背部,讨论到插图与封面设计时,编辑和作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奈达——那个给三越百货画广告的画家,很喜欢在人、物之上建造另一层人、物。朱奈达觉得物件也好,建筑物也好,都是灌满使用者、居住者记忆的容器,而记忆又能以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的形式呈现,多么适配福音馆正在推进的这本童话集。
朱奈达。这位看似神秘且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其实有其质朴、极具行动力的一面。为了打破绘本的固定观念,朱奈达每部作品都不一样,探索着不同的核心形式;为了确保创作的自由,他自己开书店和画廊,出版、展示自己的作品;而当他的作品已经获得成功,再无出版和展览方面的困扰后,朱奈达果断地关闭了书店,投身新的未来。在早年玩乐队时期,朱奈达的理念就是:“不要被固定观念抓住,不区分特定的类别,让流行、摇滚、打击乐与电子音乐交织。”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奈达是如何用行动在绘本领域践行他这一核心理念,不断突破,并且将肆无忌惮地去想象的力量交到每一个读者的手中。本文也是新京报小童书系列专栏“写童书的人”中的一篇。在这个专栏中,我们尽量全面、准确地讲述创作者们的人生故事,尝试探究那些极具原创性的童书,到底是如何从作者的性格、生命体验中生长出来的。而且我们相信:看见不同的人生,或许能让我们的心中有更多的活法,不至于被当下的诸多定义、规则束缚。该专栏即将结集成书,敬请期待。画一本难以被归类、没有标准答案的绘本在出版绘本之前,朱奈达已经作为插画师工作多年,出过十几本画集,是小有名气的画家。2016年,福音馆书店正在策划一本幻想性很强的儿童文学作品《从背中町走来》,故事的舞台背中町坐落在年老海王的背部,讨论到插图与封面设计时,编辑和作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朱奈达——那个给三越百货画广告的画家,很喜欢在人、物之上建造另一层人、物。朱奈达觉得物件也好,建筑物也好,都是灌满使用者、居住者记忆的容器,而记忆又能以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的形式呈现,多么适配福音馆正在推进的这本童话集。 朱奈达给三越百货画的广告画。编辑找到朱奈达,插画合作谈得很愉快,还有意外收获,聊天中朱奈达说起自己曾想画这样一本绘本:表面上没有故事,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书中自由生长,各不相同的人在书中自由居住,无论从哪里开始读、无论怎么读,每次读都有新发现。朱奈达的构想很快有了实体,也就是他的第一本绘本《路》。这本绘本没有文字,男孩从左端出发,女孩从右端启程,翻过一页又一页主题不同、道路近似迷宫的城市……看起来像迷宫游戏书,仔细读却发现它也不算迷宫,不管你怎么走,总能通过这座城市,走去下一个城市。而每一条街道角落里,有许多活生生的,似乎怀揣着自己故事的居民。
朱奈达给三越百货画的广告画。编辑找到朱奈达,插画合作谈得很愉快,还有意外收获,聊天中朱奈达说起自己曾想画这样一本绘本:表面上没有故事,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书中自由生长,各不相同的人在书中自由居住,无论从哪里开始读、无论怎么读,每次读都有新发现。朱奈达的构想很快有了实体,也就是他的第一本绘本《路》。这本绘本没有文字,男孩从左端出发,女孩从右端启程,翻过一页又一页主题不同、道路近似迷宫的城市……看起来像迷宫游戏书,仔细读却发现它也不算迷宫,不管你怎么走,总能通过这座城市,走去下一个城市。而每一条街道角落里,有许多活生生的,似乎怀揣着自己故事的居民。 《路》,作者: [日] 朱奈达,译者: 浪花朵朵,出品方: 后浪,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9月。创意足够奇怪,又足够有趣,值得一遍又一遍地品读,它打动了编辑,让编辑也热血、“任性”了起来——据编辑说,福音馆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绘本,选题会通过得很艰难,对接的书店也不看好,店员们纷纷发愁:都不知道怎么卖这本书,到底是艺术书还是绘本,是给成人看的还是给孩子看的呢?这个困扰出版方的问题,从未困扰过朱奈达,或者说,早在1997年,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因如此,朱奈达才会在20年后“想要画一本绘本”。1997年,朱奈达还是正在备考美术学校的高三生,他在常去的画室书架上翻到了一本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展图册,可爱的、恐怖的、尖锐的……作品风格的多样程度令他大吃一惊,也让他对于绘本“就是逗逗小孩的”这个刻板印象“啪”地一下破裂了。绘本为什么非得要划分得一清二楚呢?在唱片店里朋克音乐的架子上翻到摇滚音乐,不也一样听得开心吗?不仅不受分类问题的困扰,朱奈达反而希望自己的绘本能变得分类暧昧。年少时喜欢探索未知的道路的朱奈达,确信孩子们会享受在《路》中自由探索的乐趣。他也希望成年人能够借助阅读《路》,重启自己的想象之力。想象主人公和图画中的居民有何互动,那两个人是恋人还是朋友,两位主人公会命中注定地相遇,还是会擦肩而过……这本书没有任何“标准答案”。
《路》,作者: [日] 朱奈达,译者: 浪花朵朵,出品方: 后浪,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9月。创意足够奇怪,又足够有趣,值得一遍又一遍地品读,它打动了编辑,让编辑也热血、“任性”了起来——据编辑说,福音馆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绘本,选题会通过得很艰难,对接的书店也不看好,店员们纷纷发愁:都不知道怎么卖这本书,到底是艺术书还是绘本,是给成人看的还是给孩子看的呢?这个困扰出版方的问题,从未困扰过朱奈达,或者说,早在1997年,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因如此,朱奈达才会在20年后“想要画一本绘本”。1997年,朱奈达还是正在备考美术学校的高三生,他在常去的画室书架上翻到了一本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展图册,可爱的、恐怖的、尖锐的……作品风格的多样程度令他大吃一惊,也让他对于绘本“就是逗逗小孩的”这个刻板印象“啪”地一下破裂了。绘本为什么非得要划分得一清二楚呢?在唱片店里朋克音乐的架子上翻到摇滚音乐,不也一样听得开心吗?不仅不受分类问题的困扰,朱奈达反而希望自己的绘本能变得分类暧昧。年少时喜欢探索未知的道路的朱奈达,确信孩子们会享受在《路》中自由探索的乐趣。他也希望成年人能够借助阅读《路》,重启自己的想象之力。想象主人公和图画中的居民有何互动,那两个人是恋人还是朋友,两位主人公会命中注定地相遇,还是会擦肩而过……这本书没有任何“标准答案”。 《路》内文图。《路》里不使用文字,正是为了不让文字限制读者想象的自由度。朱奈达甚至期盼读者别把绘本当绘本,而是将它视作游戏道具,自己,或者是和亲人朋友一起,用想象创造自己版本的奇妙且奇异的世界。“我把想象的喜悦像接力棒一样交到读者手中,等某一天读者把这根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个人,这本绘本才算真正意义上完成!”在朱奈达看来,读者借由自己的绘本创造自己的世界,才是绘本得以成立的证明。这本分类暧昧的绘本在编辑的信任下,得以在2018年成功出版,而且并没有像书店店员预测的那么难卖。成人读者很喜欢,小读者也是,有一次编辑在书店布置朱奈达的宣传板,听到一个小朋友大老远就在喊“我知道那个人,我知道那个人!”实际上,店员们自己也很喜欢,纷纷写文推荐,《路》因此拿到了由书店店员投票产生的“MOE绘本书店大奖”。向正在成型的普遍想象投出一块石头《路》大获成功后,朱奈达提出一个新的绘本构想,却和此前的“无字绘本”截然相反,其核心是“文字游戏”。有一天,他偶然意识到,“的”是一个神奇的介词,它可以表达“在里面”“在上面”“从属于”等各种关系,无论本身关系多遥远的两样东西,总能借助“的”黏合在一起。朱奈达立刻试验了起来,从“我”开始,想到自己常画的那个红衣女孩,又试图让“的”变得更有魔力,于是,他想到往女孩的口袋里置入一点普通口袋装不下的奇怪东西,比如城堡,又把城堡里的床单变成大海,再到马戏团、森林、图书馆、云端、小鸟时钟、银河尽头、巨人画布、纸飞机公主……
《路》内文图。《路》里不使用文字,正是为了不让文字限制读者想象的自由度。朱奈达甚至期盼读者别把绘本当绘本,而是将它视作游戏道具,自己,或者是和亲人朋友一起,用想象创造自己版本的奇妙且奇异的世界。“我把想象的喜悦像接力棒一样交到读者手中,等某一天读者把这根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个人,这本绘本才算真正意义上完成!”在朱奈达看来,读者借由自己的绘本创造自己的世界,才是绘本得以成立的证明。这本分类暧昧的绘本在编辑的信任下,得以在2018年成功出版,而且并没有像书店店员预测的那么难卖。成人读者很喜欢,小读者也是,有一次编辑在书店布置朱奈达的宣传板,听到一个小朋友大老远就在喊“我知道那个人,我知道那个人!”实际上,店员们自己也很喜欢,纷纷写文推荐,《路》因此拿到了由书店店员投票产生的“MOE绘本书店大奖”。向正在成型的普遍想象投出一块石头《路》大获成功后,朱奈达提出一个新的绘本构想,却和此前的“无字绘本”截然相反,其核心是“文字游戏”。有一天,他偶然意识到,“的”是一个神奇的介词,它可以表达“在里面”“在上面”“从属于”等各种关系,无论本身关系多遥远的两样东西,总能借助“的”黏合在一起。朱奈达立刻试验了起来,从“我”开始,想到自己常画的那个红衣女孩,又试图让“的”变得更有魔力,于是,他想到往女孩的口袋里置入一点普通口袋装不下的奇怪东西,比如城堡,又把城堡里的床单变成大海,再到马戏团、森林、图书馆、云端、小鸟时钟、银河尽头、巨人画布、纸飞机公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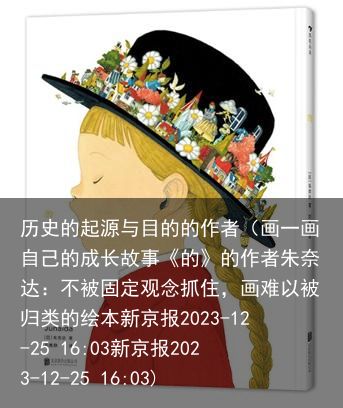 《的》,作者: [日] 朱奈达,译者: 刘雅静,出品方: 后浪,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时间: 2023年10月。从图像上归类,《的》又是一本变焦绘本。这类绘本把动态的摄像镜头艺术和静态的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通过镜头拉近、拉远讲故事,从一开始就是绘本世界里的先锋派,也诞生了不少经典作品,比如《变焦》《海底的秘密》《小红书》。而朱奈达没有遵循镜头有规律变焦这一惯例,《的》的场景时而现实,时而虚幻,空间时而磅礴,时而袖珍,入口也没有那么清晰可见,有时隐藏在未翻盖的衣兜里,以至于读者永远猜不透这一页最后一个“的”字,会在下一页连接什么样的东西,可等翻到下一页,又觉得和上一页关系如此紧密。《的》像是一部奇幻动画长片,钻进一个小洞,结果来到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恍若一层层变幻莫测的梦境,嵌套的方式没什么道理。当你以为这梦境要没完没了的时候,它又巧妙地落幕在绿衣服花冠帽子女孩的口袋里的“我”,让一直坠落又好像一直上升的读者,轻盈地脚落实地。(不过,最后的“我”也可以紧接封面上的“的”,从而变成无始无终的巡游——这是装帧设计师最终决定让书名字号和内文字号大小差不多的原因。)朱奈达的创意挑战还在继续,2020年,他在第三本绘本《怪物园》里有意识地挑战人们的刻板观念。怪物不小心闯进了城市,在大街上漫游前行,人类小孩只能躲在家里,用一个大纸箱子玩想象游戏。
《的》,作者: [日] 朱奈达,译者: 刘雅静,出品方: 后浪,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时间: 2023年10月。从图像上归类,《的》又是一本变焦绘本。这类绘本把动态的摄像镜头艺术和静态的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通过镜头拉近、拉远讲故事,从一开始就是绘本世界里的先锋派,也诞生了不少经典作品,比如《变焦》《海底的秘密》《小红书》。而朱奈达没有遵循镜头有规律变焦这一惯例,《的》的场景时而现实,时而虚幻,空间时而磅礴,时而袖珍,入口也没有那么清晰可见,有时隐藏在未翻盖的衣兜里,以至于读者永远猜不透这一页最后一个“的”字,会在下一页连接什么样的东西,可等翻到下一页,又觉得和上一页关系如此紧密。《的》像是一部奇幻动画长片,钻进一个小洞,结果来到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恍若一层层变幻莫测的梦境,嵌套的方式没什么道理。当你以为这梦境要没完没了的时候,它又巧妙地落幕在绿衣服花冠帽子女孩的口袋里的“我”,让一直坠落又好像一直上升的读者,轻盈地脚落实地。(不过,最后的“我”也可以紧接封面上的“的”,从而变成无始无终的巡游——这是装帧设计师最终决定让书名字号和内文字号大小差不多的原因。)朱奈达的创意挑战还在继续,2020年,他在第三本绘本《怪物园》里有意识地挑战人们的刻板观念。怪物不小心闯进了城市,在大街上漫游前行,人类小孩只能躲在家里,用一个大纸箱子玩想象游戏。 《怪物园》原版封面。或许会有读者想起经典绘本《野兽国》,马克斯在现实世界里和妈妈吵了架,于是通过想象进入了野兽们的世界。然而在朱奈达笔下,怪物们出没的灰暗城市是现实世界,孩子们浪游的明亮场所才是想象世界。“这种意想不到、奇怪的感觉,正是我要创造的。”虽然题材、形式、画风各异,《的》与《怪物园》却在某一点上延续了《路》的路线。当年朱奈达坚持绘本无需区分“给大人看”还是“给孩子看”,想把绘本变成所有人都能不受界限束缚而享受的东西。而此刻,朱奈达说,“现在的绘本,有一种作用是向正在成为普遍想象的东西,投出一块石头,尝试去做改变。”为了创作的自由,自己开书店和画廊在2004年的小展览中,朱奈达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根据感觉创作的人。”无论是画画、音乐、与人接触,都在创造感觉,当他在桌上摆好纸和笔,会先闭上眼睛,让感觉流动,变成波浪,直到冲撞成图像。这种凭借感觉创作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前两年的对谈中,朱奈达再次提到自己创作的时候,日常中闭锁着的纯然感性的心门会完全打开,在这种状态下,除了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画画,全身心投入其中。从具体的生活里汲取抽象感觉,再把它们塑成图像的方式,令朱奈达无意中创作了几类固定意象:门与钥匙、马戏团、音乐、书……这些物件不仅承载着作品中人物的记忆,也凝缩着朱奈达自己的记忆。比如,《的》中在森林图书馆的书架上翻看图书的刺猬,便会让熟悉朱奈达的读者想起他的另一个身份——京都鸭川河畔“刺猬书店&画廊”(Hedgehog Books&Gallery)的店长。
《怪物园》原版封面。或许会有读者想起经典绘本《野兽国》,马克斯在现实世界里和妈妈吵了架,于是通过想象进入了野兽们的世界。然而在朱奈达笔下,怪物们出没的灰暗城市是现实世界,孩子们浪游的明亮场所才是想象世界。“这种意想不到、奇怪的感觉,正是我要创造的。”虽然题材、形式、画风各异,《的》与《怪物园》却在某一点上延续了《路》的路线。当年朱奈达坚持绘本无需区分“给大人看”还是“给孩子看”,想把绘本变成所有人都能不受界限束缚而享受的东西。而此刻,朱奈达说,“现在的绘本,有一种作用是向正在成为普遍想象的东西,投出一块石头,尝试去做改变。”为了创作的自由,自己开书店和画廊在2004年的小展览中,朱奈达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根据感觉创作的人。”无论是画画、音乐、与人接触,都在创造感觉,当他在桌上摆好纸和笔,会先闭上眼睛,让感觉流动,变成波浪,直到冲撞成图像。这种凭借感觉创作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前两年的对谈中,朱奈达再次提到自己创作的时候,日常中闭锁着的纯然感性的心门会完全打开,在这种状态下,除了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画画,全身心投入其中。从具体的生活里汲取抽象感觉,再把它们塑成图像的方式,令朱奈达无意中创作了几类固定意象:门与钥匙、马戏团、音乐、书……这些物件不仅承载着作品中人物的记忆,也凝缩着朱奈达自己的记忆。比如,《的》中在森林图书馆的书架上翻看图书的刺猬,便会让熟悉朱奈达的读者想起他的另一个身份——京都鸭川河畔“刺猬书店&画廊”(Hedgehog Books&Gallery)的店长。 《的》内文图照片。2010年6月,朱奈达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刺猬书店开业的消息,他说:“今后我会以朱奈达(Junaida)为名,以刺猬书店(Hedgehog)为据点,尝试做各种各样快乐的事情。”——这是朱奈达走出迷茫期的起点。上大学时的朱奈达无疑是迷茫的,明明喜欢画画,对技艺也有自信,却偏偏无心画画,反倒是全身心玩起了乐队。在他看来,那时候的作品回顾起来缺乏灵魂,绝对不会示众。2001年从京都精华大学漫画学部毕业后,朱奈达一边当自由插画师,给包括时尚杂志、警察局在内的各种机构画插画,一边继续玩乐队。2004年是朱奈达职业生涯上的第一个变化期,他参加了艺人事务所“AMUSE”主办的艺术奖,并在之后进入“AMUSE”事务所当专职插画师。
《的》内文图照片。2010年6月,朱奈达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刺猬书店开业的消息,他说:“今后我会以朱奈达(Junaida)为名,以刺猬书店(Hedgehog)为据点,尝试做各种各样快乐的事情。”——这是朱奈达走出迷茫期的起点。上大学时的朱奈达无疑是迷茫的,明明喜欢画画,对技艺也有自信,却偏偏无心画画,反倒是全身心玩起了乐队。在他看来,那时候的作品回顾起来缺乏灵魂,绝对不会示众。2001年从京都精华大学漫画学部毕业后,朱奈达一边当自由插画师,给包括时尚杂志、警察局在内的各种机构画插画,一边继续玩乐队。2004年是朱奈达职业生涯上的第一个变化期,他参加了艺人事务所“AMUSE”主办的艺术奖,并在之后进入“AMUSE”事务所当专职插画师。 朱奈达早年为自己乐队画的专辑封面。做专职插画师,就不能在作品里投入太多个人属性,必须以客户需求为准,更何况所在公司又不是专业经营美术经纪的公司。虽然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同伴也都很优秀,朱奈达却无所适从,“并不是说专职插画师职业有问题,我身边优秀的插画师们很擅长应对客户的需求……我渐渐觉得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做插画师,更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画自己的画。”以“感觉”为画笔的画家,很难适应以“需求”为准则的插画工作。刺猬书店是为了把画画和生计拆分开而开业的。书店里售卖各种图书与杂货,本身就是盈利的。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展览空间,有时展陈朱奈达自己的作品,有时则是其他插画师的画。如此一来,如果自己想画的画没地方愿意展陈,那就放在刺猬书店;假如出版社不愿和他一起挑战闻所未闻的创作,也能以刺猬书店的名义出版;如果作品没有好到吸引人购买,也总有人愿意买一张明信片、一个徽章,而这同样是一种认可。几乎可以说,书店就像尖刺,保护着朱奈达创作的自由——而这就像刺猬柔软的肚皮。朱奈达得以用自己舒适的感觉创作法,把自己对于生活感觉的记忆,变形成图像,去表达物件、建筑是装载人们记忆的容器这一想法。沿着这一方向前进,才有了此后引起福音馆编辑关注的三越百货广告画,以及画下《路》《的》《怪物园》的朱奈达。想描绘超越现在的未来,于是再一次出发2021年6月,书店开业11周年之际,朱奈达宣布关闭线下店铺。“‘刺猬’随着我们的成长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我们想要描绘超越这种变化的未来时,作为门店的‘刺猬’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是时候进入下一步了。第10周年时我就有了这种预感。”紧接着的7月,朱奈达出版了一本新绘本《城市小偷》。这是朱奈达创作的绘本中最接近一般故事绘本形态的作品,故事超越了图像与感觉,成为了绘本的主角。山顶上住着一位孤独的巨人,某个晚上,巨人寂寞得没有办法了,便去山脚下的城市偷了一座房子回来。巨人请求这一家人:“从今往后我们就在这里一起生活吧。你们要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无论什么我都会带给你们。”
朱奈达早年为自己乐队画的专辑封面。做专职插画师,就不能在作品里投入太多个人属性,必须以客户需求为准,更何况所在公司又不是专业经营美术经纪的公司。虽然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同伴也都很优秀,朱奈达却无所适从,“并不是说专职插画师职业有问题,我身边优秀的插画师们很擅长应对客户的需求……我渐渐觉得自己的个性不太适合做插画师,更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画自己的画。”以“感觉”为画笔的画家,很难适应以“需求”为准则的插画工作。刺猬书店是为了把画画和生计拆分开而开业的。书店里售卖各种图书与杂货,本身就是盈利的。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展览空间,有时展陈朱奈达自己的作品,有时则是其他插画师的画。如此一来,如果自己想画的画没地方愿意展陈,那就放在刺猬书店;假如出版社不愿和他一起挑战闻所未闻的创作,也能以刺猬书店的名义出版;如果作品没有好到吸引人购买,也总有人愿意买一张明信片、一个徽章,而这同样是一种认可。几乎可以说,书店就像尖刺,保护着朱奈达创作的自由——而这就像刺猬柔软的肚皮。朱奈达得以用自己舒适的感觉创作法,把自己对于生活感觉的记忆,变形成图像,去表达物件、建筑是装载人们记忆的容器这一想法。沿着这一方向前进,才有了此后引起福音馆编辑关注的三越百货广告画,以及画下《路》《的》《怪物园》的朱奈达。想描绘超越现在的未来,于是再一次出发2021年6月,书店开业11周年之际,朱奈达宣布关闭线下店铺。“‘刺猬’随着我们的成长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我们想要描绘超越这种变化的未来时,作为门店的‘刺猬’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是时候进入下一步了。第10周年时我就有了这种预感。”紧接着的7月,朱奈达出版了一本新绘本《城市小偷》。这是朱奈达创作的绘本中最接近一般故事绘本形态的作品,故事超越了图像与感觉,成为了绘本的主角。山顶上住着一位孤独的巨人,某个晚上,巨人寂寞得没有办法了,便去山脚下的城市偷了一座房子回来。巨人请求这一家人:“从今往后我们就在这里一起生活吧。你们要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无论什么我都会带给你们。” 《城市小偷》原版照片。这家人便让巨人把亲戚们的房子也搬上山,亲戚们又请求巨人把他们的朋友的房子也搬上山,直到几乎整个城市都被搬到了山顶上,大家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然而巨人的寂寞并未消解,他决定独自下山。在山脚下的城市,还有一个男孩和他的房子……朱奈达为这本绘本写了一篇长长的创作手记,因为写下这个故事后,他意识到也许这是个写给儿时自己的故事。朱奈达小时候经常转学,不管身处哪里,都感觉脚下空落落的,好像自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倒也不是没交过朋友,只是感觉不熟悉那片土地,和周围人是不一样的,不属于那里。他对当年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种感受印象深刻,如今,这种感受以蹲坐在城市之间的孤独巨人的形象复现。“我想,这个故事里的巨人会抵达的所在,每个人的想象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当年的我来说,那个所在是音乐。14岁第一次听朋克音乐时,我感觉自己和世界相接的那道门第一次打开了。”但如今看来,朋克音乐不是朱奈达与世界连接的终点,创造了快乐回忆的刺猬书店也不一定是终点。“我们会在和人相遇中找到门钥匙,遇到和自己有共鸣的人或事,就算踏出了第一步。但找到钥匙并不容易,你也可以试着去别的地方,不必停留在哪里,继续往前走就好。”像巨人决定下山,就像《路》的主人公也可以选择擦肩而过,继续自己的探索,就像《的》的无始无终,喜欢打破普遍想象的朱奈达从不满足于停留于某处,他选择继续寻找新的可能性。近两年间,朱奈达在佐仓市立美术馆等大型美术馆举办了个展,并计划全国巡展。他的确正在描绘超越过去的未来。参考资料:1.朱奈达个人官网https://www.junaida.com/2.HOBO×朱奈达专访https://www.1101.com/junaida/2015-06-09.html3.《的》日版出版对谈(祖父江慎×朱奈达)https://www.fukuinkan.co.jp/blog/detail/?id=4494.《城市小偷》作者创作手记https://www.fukuinkan.co.jp/blog/detail/?id=5025.福音馆编辑冈田望专访https://play2020.jp/article/junaida_interview_okada_3/ 撰文/吴回音编辑/王铭博校对/薛京宁举报/反馈
《城市小偷》原版照片。这家人便让巨人把亲戚们的房子也搬上山,亲戚们又请求巨人把他们的朋友的房子也搬上山,直到几乎整个城市都被搬到了山顶上,大家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然而巨人的寂寞并未消解,他决定独自下山。在山脚下的城市,还有一个男孩和他的房子……朱奈达为这本绘本写了一篇长长的创作手记,因为写下这个故事后,他意识到也许这是个写给儿时自己的故事。朱奈达小时候经常转学,不管身处哪里,都感觉脚下空落落的,好像自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倒也不是没交过朋友,只是感觉不熟悉那片土地,和周围人是不一样的,不属于那里。他对当年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种感受印象深刻,如今,这种感受以蹲坐在城市之间的孤独巨人的形象复现。“我想,这个故事里的巨人会抵达的所在,每个人的想象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当年的我来说,那个所在是音乐。14岁第一次听朋克音乐时,我感觉自己和世界相接的那道门第一次打开了。”但如今看来,朋克音乐不是朱奈达与世界连接的终点,创造了快乐回忆的刺猬书店也不一定是终点。“我们会在和人相遇中找到门钥匙,遇到和自己有共鸣的人或事,就算踏出了第一步。但找到钥匙并不容易,你也可以试着去别的地方,不必停留在哪里,继续往前走就好。”像巨人决定下山,就像《路》的主人公也可以选择擦肩而过,继续自己的探索,就像《的》的无始无终,喜欢打破普遍想象的朱奈达从不满足于停留于某处,他选择继续寻找新的可能性。近两年间,朱奈达在佐仓市立美术馆等大型美术馆举办了个展,并计划全国巡展。他的确正在描绘超越过去的未来。参考资料:1.朱奈达个人官网https://www.junaida.com/2.HOBO×朱奈达专访https://www.1101.com/junaida/2015-06-09.html3.《的》日版出版对谈(祖父江慎×朱奈达)https://www.fukuinkan.co.jp/blog/detail/?id=4494.《城市小偷》作者创作手记https://www.fukuinkan.co.jp/blog/detail/?id=5025.福音馆编辑冈田望专访https://play2020.jp/article/junaida_interview_okada_3/ 撰文/吴回音编辑/王铭博校对/薛京宁举报/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