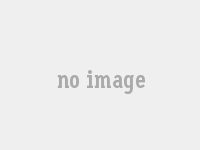永不消失的电波属于什么题材(成长故事9[80后成长故事]9. 永不消失的电波)
收音机
看不到CCTV5,是我回到泾阳后最令人沮丧的事情。虽然离县城只有咫尺之遥,但老家的村子却迟迟没有接通有线电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爸曾试图去买一个接收卫星信号的设备,可以架设在房顶,当地人俗称为“锅”。但令人遗憾的是,通过“锅”虽然能看到不少卫视频道,却偏偏解码不了央视5套。承担不菲的价格还有合规风险(私装卫星接收器是不被允许的),却不能解决核心痛点问题,这套方案最终也不了了之。
 “锅”
“锅”告别每天的《体坛快讯》和《体育世界》,我几乎出现了戒断反应,那种百爪挠心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很久。找到新的精神食粮,源于一次意外的活动,一个同学送了我一个二手的调频收音机,非常小巧,只有两个打火机大小。在这之前我见过的“收音机”,要么是带着两个大喇叭、可以录播磁带的收录机,要么是老头老太太们听戏用的“黑匣子”,这么袖珍且有时尚感的收音机我还是第一次见。可以收听到的内容也让我很惊喜,音质比我刻板印象中的广播要清晰很多(其实是FM调频和AM调幅的区别,前者传播距离有限,但也不太容易受到噪声的影响),而且可以收到的频道有十几种之多,大大超出我的预期——这是离省会近的好处,可以收到西安的各种电台,印象中我在榆林也摆弄过家里的收录机,但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声音。
从那以后,广播成了我新的心理寄托,看书写字也要带着耳机,这个习惯贯穿了整个初中和高中时期,收音机设备也前前后后用坏了好几个。父母没少念叨我“一心不能二用”,但我坚称这有益于学习,仗着良好的KPI,也并没有受到实际的干预。
印象深刻的主播与节目
对于广播节目,我几乎来者不拒,从音乐打榜到情感夜话,从交通路况到评书相声,午夜各种生理健康热线也照单全收,各个频道的节目单早已了然于胸,连片花口播都记得烂熟。
当然,广泛涉猎之下也有偏爱,陕广“财富广播”是我听得最多的频道,每天下午6点有一档综艺类节目,集段子、智力问答、点歌等形式为一体,主持人叫王乐,擅长插科打诨,在罐头笑声的配合下很有节目效果。他周末偶尔还会出现在一些体育类节目中,我也相当喜欢,比如,印象中就听过他播讲的纪念罗伯特·巴乔的长文,有点央视《天下足球》的范儿。他有两个经常配合的搭档,一个叫岳磊,是个体育主播兼记者,自我介绍总会说自己的“岳”是“岳武穆的岳”;另一个女主持人是个“捧哏”角色,已经记不起名字了。到了晚上9点之后,财富广播还会有另一档受众颇广的情感热线,叫《长安夜话》,家长里短,爱恨情仇,听多了会让人有种“众生皆苦”的沧桑感。主持人叫力闻,声音浑厚低沉,磁性十足,遇见想不开的听众会劈头盖脸骂一顿,颇具威严,让人透过电波能自动脑补出一副金刚怒目的面容。他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毫无征兆,令人扼腕。
一般来说,我对比较搞怪的主播会更加关注,多年之后还有印象的也多是此类。西安交通广播午间有个智力问答,主持人杨凯会压着嗓子扮演两个卡通人物,咖啡猫(没错,不是“加菲猫”,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规避版权)和他的主人,反差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开了变声器。有一段时间各地流行给《猫和老鼠》做方言配音,关中话版就是他配的,但播了几集,广电就把这股风气叫停了,理由是不符合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有些可惜。印象中还有一个主持音乐点播节目的男主持人,听过不少却实在想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他用嘶哑的嗓音去念“七度空间”卫生巾的冠名广告,有一种莫名的反差喜感。
除了本地的节目之外,当时陕广部分电台还会转播一些全国其他地区的优秀节目,比如北京交通台的《欢乐正前方》和辽宁台的《娱乐双响炮》,这两档节目都是笑话集锦,我都很喜欢,有一次偶然看到《欢乐正前方》的主持人王为在一档电视节目上出镜,感到非常惊喜,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这叫“打破次元壁”。
这些主持人让我一度觉得电台主播是个非常让人向往的职业,不仅有趣,而且每天只需要工作一两个小时,非常自由。不过我自忖言语迟钝,即便后天再努力恐怕也难有建树,这个愿望只好留在白日梦里。

电波中的“伊斯坦布尔之夜”
还有一些小片段很有意思,05年欧冠决赛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在咸阳上高中,虽然已经具备看CCTV5的物理条件,但一则由于时间太晚,二则就AC米兰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而言,还不足以配上国足的“待遇”,所以我选择躺在床上听电台的直播。3:0之后我就睡着了,结果众所周知,第二天看到新闻大跌眼镜。在很多米兰球迷的“口述历史”中,都有类似的一段回忆,不同的是,我的经历中扮演媒介的是耳朵与广播,而非眼睛与电视。
没听完的“奇迹”
当年,歌手满江发过一张专辑叫《奇迹》,在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其实并不起眼,不过这张专辑附带了一个故事,我在电台里听过好几次,不过好巧不巧,每次都没能听完结尾,我后来推测原因可能是这个故事时长刚好超过一个小时,一个典型电台节目不足以容纳。那是一个分分合合的言情剧,亮点是旁白有种痞气的幽默感,故事本身并没有非常精彩,但每次都听不到结尾就成了一种遗憾,逼死强迫症般令人抓狂。至今我也没有去听过结局,说不定写完这篇文章会有兴致去找来弥补一下。
“偷听敌台”
高中的时候,有天意外的发现可以收听到对岸的“中央广播电台”,不过收听的条件非常苛刻,需要把收音机调整到一个微妙的角度,在中波的某一个角落里仔细搜寻,才能勉强捕捉到细若游丝的信号。这个发现令人既震撼又惊喜,我爸常开玩笑说“偷听敌台”,没想到“敌台”还真让我给找着了!听了几次后发现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发嗲的台湾腔和体育新闻中“中华民国队”的称谓让人有些新鲜感外,其余内容大同小异,我在听了一段时间的晚间校园剧之后,就提不起太多兴趣了。
飞鱼与鱼
听广播的热情在大学期间渐渐消退了,属于无疾而终——上海的电台水平其实相当不错,种类也更加丰富,但我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喜欢的频率,随着互联网的访问越来越便利,广播逐渐成为资讯生活中的配角。在最后的电台时光里,经常听到的两首歌是苏打绿的《飞鱼》和陈绮贞的《鱼》,一首坚韧励志、奋发向上,一首晦涩挣扎、挥别过往,照进我当时的生活,倒是分外的应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