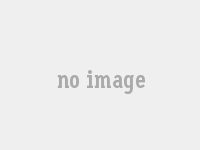梅州星儿家园训练中心(家庭成长故事“希望活得比孩子久!”梅州4个“星儿家庭”的故事,让人泪目)
2023年4月2日是第16个世界孤独症日。据统计,中国孤独症群体超过1100万人,被称为“星儿”的孤独症儿童200多万人,约每10000名儿童中有107名孤独症儿童。
在梅州,也有这样的群体。为了孩子,有的家庭爸爸一人扛下赚钱养家的重担,妈妈则当起了全职妈妈,陪着孩子康复、感知世界;有的父母既要忙于工作,还要带着孩子四处求医,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超人。

“星妈”带着“星儿”走在就医路上。受访者供图
然而由于许多人对于“孤独症”并不了解,孤独症孩子常被认为是异类,生活中屡屡碰壁,遭遇不公与排挤。“星儿家庭”更备受考验与煎熬。
“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发声,没人知道我们究竟遭受着什么、我们的孩子面临着怎样的处境。”4月2日这天,梅州4个“星儿家庭”选择接受媒体采访,说出了他们的经历。
“得知孩子生病,天塌了”
“眼神很飘,坐不住。”在幼儿园老师提醒下,胡蓉花带着孩子到广州看病。拿到孩子的诊断书的那一刻,胡蓉花先是一愣,随后情绪崩溃嚎啕大哭。
站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高层,胡蓉花想一跃而下。排队三个月,看病十来分钟,专家就下了结论。
“孤独症”三个字冷冰冰地写在纸上,就如同宣告了孩子一生的结局。这一结果,过于残酷。后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胡蓉花始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孤独症是一种持续终身的障碍,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言语发育障碍、人际交往障碍、兴趣狭窄和行为方式刻板。这些特征,儿子小佑都有。

“星儿”们在进行康复训练。受访者供图
“我该怎么办?”“我的孩子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胡蓉花想不通,自己和先生都是本科毕业,都有体面的工作,往上查三代也无此病,为何孩子会有此病。
小佑8个月时确诊血友病,隔天就得输入凝血因子,6岁又被确诊为孤独症。胡蓉花可怜孩子小小年纪就如此遭罪。
“不要大惊小怪,也许是医生误诊,孩子长大后就会好的。”爷爷奶奶不理解何为孤独症,以为长大就是一剂良药。“你就是太少带他出去玩了。”亲戚好友们也不理解,善意的安慰下甚至带点埋怨。
胡蓉花与爱人从广州带回了厚厚的一摞资料,对于孤独症,两人也不了解。“专家没说有什么药可治,只说要做干预训练。”回来后,胡蓉花与爱人便开始疯狂啃食知识,在网上搜索梅州当地的康复机构。
“梅州的孤独症康复机构太少了,找了很久,才找到了星儿家园的王老师。”那一刻,胡蓉花感觉抓到了救命稻草。
尽管在系列干预之下,小佑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在众多孩子之中,还是能一眼就看出他的不同。
自言自语、傻笑、眼神不对焦……越长大,孤独症带给这个家庭的困扰就越多,尤其是在教育上。
“没人愿意跟他一起玩,老师天天投诉。”为了让孩子能继续留在学校,胡蓉花与爱人每天晚上都要花上数倍努力,为孩子补习功课。
“进入初中后,差距就很明显了,比如语文,他没办法理解那些深层次的意思。”胡蓉花说,课堂坐不住等情况也会给老师带来困扰,需要不停解释。
“星儿家庭”们也想过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特殊学校,但梅州各级特殊学校招收孤独症儿童的少之又少。留在普校或到康复机构成了少有的选项。

“星儿”学习坐公交车。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究竟是让孩子继续待在普校,还是办理退学、早日开始职业规划与技能培训,是大龄“星儿”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是孩子跟不上学校的步伐,另一方面是家长们希望孩子能在学校学习社会规则。选择的压力不仅于此,亲戚朋友们的劝说也让“星儿家庭”不得不慎重考虑。
“这个年龄段不读书能干嘛?”“再难也要读完初中。”在得知胡蓉花有意向让孩子休学后,身边人都强烈反对。
有了小佑,胡蓉花不敢再生第二胎。一是因为二胎孤独症患病几率更高,“二是我觉得这样对二胎不公平,他就是他,不是生下来照顾哥哥的。”胡蓉花说。
“希望自己活得比孩子久”
2017年的4月2日,对于林英一家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这一天,是林英爱人的生日、也是女儿小恩确诊的日子、还是世界孤独症日。
2岁7个月时,小恩确诊为孤独症。此前,身为医务工作者的林英已经发现了孩子的异常:一岁多还不会说话、不会表达需求、打雷下雨没反应……
女儿确诊时,林英已有三个月身孕。尽管在医院看多了生老病死,但得知女儿被确诊患有孤独症的那一刻,林英承受不住打击,先兆流产,一躺就是好几个月。
孤独症儿童常常伴有睡眠障碍,小恩也是如此。常常是早上七点醒,晚上一两点才睡。为了哄孩子入睡,林英与爱人只能把哭闹的孩子绑在车里的安全座椅,整个梅城地兜,才让她入睡。

为了孩子,林英请假三个月,北上青岛,带着孩子在国内较为前沿的康复机构进行康复训练。三个月后,爸爸接替妈妈,再三个月,爷爷奶奶接替爸爸,全家总动员,在青岛陪着孩子进行了两年的干预训练,前后花费五六十万元。
付出是为了什么?父爱母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当孩子开口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林英说。
幸于及早与坚持不懈的干预,小恩从中度孤独症向着轻度发展,从之前上课满堂跑,到如今能规矩安坐,目前已在普校上小学二年级。
与胡蓉花一样,林英也碰到了教育的难题。没入学时,林英就把孩子可能出现的症状、遇到行为问题时该怎么解决等制成PPT交给老师。
让林英揪心的是,小恩不被接纳。一年级时,小恩想当少先队员,她给自己投了一票,其他同学都给了反对票;二年级时,小恩竞选劳动委员,再次被投了反对票。回到家后,小恩伤心地哭了很久。
林英想给小恩请个“影子老师”即特教助理,帮助孩子更好融入集体,纠正行为问题,但学校以小恩能安坐,没必要陪读为由,三次拒绝了请求。
林英不是个例,目前梅州鲜少学校能接受“影子老师”。这些年来,“星儿家庭”一直在奔走疾呼。
“孤独症孩子即便在学校受欺负,也不会告状,他们无法讲述清楚事情的经过,‘影子老师’能及时录下视频,通过情景演练,告诉孩子遇到这些事情时该怎么处理。”梅州市自闭症互助协会会长廖立维表示,更为重要的是,普校教师比较少孤独症的相关知识与接触经验,“影子老师”可以引导其他学生如何接受孤独症儿童,为“星儿”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随着孩子越来越大,“星儿”该何去何从,也是不少大龄“星儿”家庭在考虑的事。林英说,“希望自己活得比孩子久。”胡蓉花则开始打听信托基金,“我愿意把房子等财产上交国家,只求国家能够照顾我的孩子。”
“撑下去,孩子才有希望”
因为儿子小豪的确诊,余晓梅加入“星儿”守护团队,成了一名特教老师。此前,她是一名生意人。
“孤独症产检检查不出来,6岁前是康复的黄金期,应及早干预。”有着多年从业经历的余晓梅对孤独症知识脱口而出。
让余晓梅下定决心从事这一行,是无数次的心酸与无力感使然。有一次,同学将吃剩的鸡骨头给小豪,小豪不仅吃下,回到家还开心地跟余晓梅说:“我同学说我是傻子。”余晓梅当即眼泪流了下来,心疼孩子的遭遇,小豪甚至连别人骂他也听不懂。
从业以后,余晓梅不仅陪着自己孩子一路披荆斩棘,也教会了许多“星儿”如何与别人相处、如何与世界相处。

“星儿”正在制作钻石画。受访者供图
她是为数不多让孩子退学的“星儿”妈妈。今年14岁的小豪如今是星儿家园大龄班的学生,目前他已学会通过制作钻石画、保洁等方式赚钱。
与众多家庭一样,孩子未来何去何从同样困扰着余晓梅一家。思考再三,一家人做出退学的决定,“我们只能护他一程,他迟早要面对社会,希望他早日学会生存技巧。”余晓梅说。
上述的三位“星儿”妈妈都有自己工作,实际上,在康复训练机构,全职妈妈占了很大一部分。刘秋华便是其中一个。来自蕉岭的她,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小洪今年5岁,在3岁时被确诊孤独症。
为了孩子,刘秋华从深圳返回梅州,在梅城租房子带着孩子进行康复治疗,而挣钱的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父亲身上。为了省钱,刘秋华与人合租,但各种花销加起来,每个月最起码过万元。
刘秋华的爱人在深圳打工,这几天放年假,特地陪着孩子到做康复,“孩子妈妈很辛苦,谁家摊上这个事都难。”他说话很简短,却有着异常的冷静与坚定。
一人打工挣钱养家、一人在家照顾孩子,为了孩子,他们选择了异地,选择了无言的付出。
“来康复机构干预前,孩子胆小,怕见人,无法交流。干预后,能与人沟通了。”点滴变化让夫妻俩看到了希望。刘秋华说,希望通过干预,未来孩子生活能自理,不受人欺负。
今年8月份,刘秋华准备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前方等待他们的,不管是何艰难险阻,夫妻俩已做好准备,“父母不能倒下,撑下去,孩子才有希望。”

“星儿”们正在制作钻石画。受访者供图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梅州不少爱心人士通过购买钻石画、提供岗位、捐助等形式向这个群体伸出了援手。但对于“星儿”们来说,干预治疗是终身的,花费也是巨大的。目前梅州7周岁以下的孤独症患者有救济补助,而7岁以上的大龄“星儿”治疗则完全靠家庭支撑。
“一些没有条件的农村家庭,只能将‘星儿’锁在家里。没有康复训练干预治疗的‘星儿’,最后有失去未来的可能性。”廖立维呼吁,社会各界能给予这个群体多点关爱与理解。
原标题:
走近梅州“星儿家庭”
“请给我的孩子多点善意”
【来源】南方日报、南方+
【南方日报、南方+记者】魏丽文
【作者】 魏丽文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