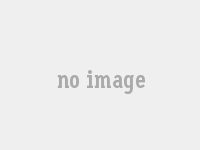幼儿成长故事视频连续播放卖火柴的小女孩(儿童成长故事超暖心的儿童成长故事!启迪智慧,让孩子勇敢迎接挑战)

黑将军
1
飞鸟把美丽的翅膀,像折扇一样收起。
父亲像落阳一般沉默,却满心欢喜。
我三步一回头,跑在前方,再回转头来看它。黑夜提前来到了它的身上,除了三角形的头顶心有一圈白色的旋转而生的毛之外,它通体漆黑。
那时,它还不叫“黑将军”,大概比我还小,刚离开了妈,三步一回头。
我望望含笑不语的太阳,它已经轻悄悄地滑到了西边的山脊,这时候,太阳和父亲一样,心满意足,不急了。
我可急坏了,见它恨不得走一步退三步,便回转奔跑,扬了扬手中的荆条杆,却舍不得抽打在它因为抗拒前行而微微撅起了尾巴的屁股上。
它的屁股饱满圆润,毛色光洁,在夕阳下闪着幽暗的微光。
它粗短结实的脖子梗着,别扭地昂起头,仿佛在看东天边最早出现的那颗最亮的星。
它漆黑的眼睛那么明亮,湿漉漉的,仿佛夏夜的露水全落在了它的眸子里,湿润而忧伤。
父亲缠着它的主人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硬是把太阳谈得渐渐失去了耐心,一头歪在了刺槐树的树梢上。再不拿主意,太阳可是要下山了。
在这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父亲曾经三次跑到一丈远的墙角,把怀里揣着的钱数了好几遍……还是那个数目,不会因为父亲数的次数多了,钱就能再多出一些。
它的主人虽然也一再让步,但是,距离双方成交还是有差距。
最后,父亲只好放弃了。
“母牛归你,我的钱,只够买这头小牛犊……”
耗了三个多小时,双方都很遗憾,但是,在清点钞票的时候,虽然疲惫,双方却也都有掩饰不住的欢喜。
我们赤脚踩踏在因为夏夜的露水而湿润了的草地上,翻越山岗。
夏虫鸣唱,脚步杂沓,呼吸粗重。
浸染了露水的万物,温润阒寂。
月亮那么明亮。
它不断地回望,也望不见妈妈。
偶尔,它会站立在月光下,明亮的眸子满是迷茫。
好几次,它昂起头来,耸动着湿润的黑鼻子,想要“哞哞”地叫,却终于什么声音都没有。
它低着头在月光下走得那么忧伤,我不知道它那时在想什么。
2
它像酣睡中被叫醒的孩子,迷迷瞪瞪地站在田野之中,大而湿润的眼睛满是迷茫。它微微仰着头,耸动着湿润油亮的黑色鼻孔。
父亲用绳子在它的头上打了个活结,没有用一根光滑的丫字形树枝穿过它的鼻孔。父亲说,它和我一样,正在生长。
初夏的风裹挟着新翻泥土的气息和花草的芬芳,让我们一起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它小心地靠近我,伸出它酱紫色的舌头舔了舔我的裤腿。
它开始低头用它细长坚韧的舌头卷起青草、野蔷薇带刺的嫩枝,还有刚刚盛开的花朵……这些,都被它的舌头卷进了口腔,很快,白色和绿色的汁液从它的嘴角溢出。
它仿佛接受了现在的命运——从此要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远离母亲。
我用一根柳条帮它驱赶油滑皮毛之上的蚊蝇,它的尾巴偶尔也会抽在我的手背上,会有一阵甜蜜而疼痛的颤栗。
像池塘里才露尖尖角的荷叶,它的额顶鼓着两个鹌鹑蛋大小的包,它的犄角即将从这里长出,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正小心地试探着用指肚去触抚它的犄角,它昂起了头,嘴巴轻微咀嚼,眼睛里有了亮晶晶的光。
它不断耸动着湿润的鼻子,分辨着夏风携带给它的消息……
烟火的气息,泥土的气息,花草的气息,太阳的气息,麦穗的气息,淡淡的农药味儿,还有飘渺的歌声,远处马路上汽车的马达声,都在这风里。
突然,它红着眼睛,别扭着脖子,要挣脱我手里的缰绳。
我绷直了双腿,伸过手去攥紧楝树的树枝,跟它讲着好话,求它别走。
我被它在草地上拖行了好远,终于,绳子从满是汗水的手心里滑落。
它微微撅起尾巴,跑成了田野里的一阵黑旋风。
我一边哭喊着追赶,一边恐惧得全身颤栗。
因为我知道这头小牛犊对于我们家意味着什么,万一它跑了再也找不到了该怎么办?它跑这么快,会不会突然飞上了天?……
好在,虽然我被它甩下好远,但始终能够看见它。
它从田野跑进松林,它迎着风,后来就成了风的一部分,没有要停歇下来的意思。
我跑得肚子一阵阵剧痛,心脏“咚咚咚”像敲门那样急切地敲击着胸腔。
它跑进松林里了,我看不见它了。
我也跑进了松林,闻见了牛群特有的味道,也隐约听见了牛的“哞”叫。
松林里有好大一群牛,它果然就是奔它们而来的。
我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一边斜着眼睛看因为它的加入而引起的牛群的骚动——它正努力地靠近一头黑色的母牛,但是,却被一头高大的公牛一头顶了个趔趄……
当它从草地上重新站立起来时,那头黑色的母牛扬起后蹄踢向了它的肚子……
我顾不得喘气,提起柳条冲进牛群,左右开弓,见牛打牛,把牛群驱散了,只剩下我的那头发呆失落的小牛犊。
突然,一声响亮的鞭子在空中炸响,那个老头骑着一头老牛,从松林的另一端过来了。
老头我早认识的,邻村的老铁头,单身汉,放牛为生,与牛为伍,靠牛吃饭。总是神神叨叨,每次见我们小孩总要骑着牛现身。
他能让一根长鞭子在空中炸响,他也能用鞭子隔着两三米的距离把柿子树上的一颗柿子打碎。
我不敢再打他的牛了,再说,那根柳条已经被我打断了。
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寒战,才知道衣服全湿透了。
我扭过头望着它,它不再去靠近那群渐行渐远的牛。只是,它不再吃草,湿润的眼角下两道泪痕把皮毛都打湿了。
这让它的眼睛那么明亮,水汪汪的,黑漆漆的。比最黑的夜还要黑,比最明亮的星还要亮。
只是那双眼睛看了就让人心碎,让人难过。我看了,中饭都吃不下,难怪,它也不想吃草了。
它奔袭追赶的那头母牛,并不是它的妈妈。
它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哪儿去了,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美丽的大眼睛只是装满忧伤。
至今悔恨,我不该和它一起发呆,应该过去,抱紧它的脖子……
3
中午一场暴雨过后,天晴了,洗干净的天空湛蓝湛蓝。
我赤着脚,半截身子都被沾满雨水的草丛打湿了。肥胖的蚂蚱鼓着翅膀“唰唰唰”地从我身边飞过,伸手去抓草叶上的蚂蚱,它带着钩刺的大腿用力蹬逃,飞了,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我的手指肚滚出一滴圆圆的血珠。
我陪伴它两年了,它快三岁了,开始换牙了。
它“呼哧呼哧”地用舌头卷起青草,然后,“噌噌噌”地生长着。
我侧耳倾听,能听见稻田里稻子拔节生长的声音,隐约间甚至能闻见提早扬花的稻花香——我甚至都能听见自己心脏“咚咚”的跳动声,还是听不见它生长的声音。
它分明就比稻子长得快嘛。
后来,听到它放了个屁,一扬尾巴,拉出了一堆油光黑亮的牛粪——差点落在了我的脚上,很快苍蝇们“嗡嗡嗡”地落了过来。
我举着手指,让太阳光把指肚上的那滴血晒干。
忽然,我双手按在它的脊背上向上跃起,我想骑在它的背上,像那个老头一样。
可是,并没有成功,它太高了。
虽然没有成功,却把它吓坏了,它愣了一下,忽然扭过头向我顶了过来。幸亏看完功夫电影后我喜欢比划比划,身手还算矫健,躲开了。
它额顶上的犄角有我手掌那么长了。
它瞪着美丽的大眼睛,漆黑的睫毛有小拇指那么长,迷惑地望着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
我比划解释了一通,也说了不少好话。
它又开始低下头来吃草,我以为它懂了。可是,我再次试图骑在它背上的时候,它仍旧扭过头来顶我,而且,这次,它成功了。
我转身奔逃的时候被它一头撞在屁股上,摔了个狗啃泥。
那个老头是怎么做到的呢?
机会终于来了,水沟里的草生长丰茂,它站在水沟里啃着沟两边的嫩草——我站在沟沿上,一抬腿就可以轻易地骑在它的脊背上……
我真的这么做了,骑在它的背上,紧张得头顶直冒汗。
它愣了好久,不知所措。
然后,它小心地从水沟里爬了上来,踩踏着奇怪的步伐,仰着头打着转儿,像是一只想要衔住自己尾巴的小狗。
转了几圈之后,它又四处张望,也不吃草了。
那时,太阳快落了,那个放牛的老头也该回来了,我多希望他能看见我啊。如果,没有他,换作任何一个人都好啊。
“快看啊,快看我,我骑在牛背上,像一个英雄……”我心里恨不得快活地喊出声来。
没有任何一个人,风也不来,太阳不见了,西天一片绚烂的晚霞。
刚跳下来,还没有站稳,它突然冲着我顶了过来,我头一仰,从它的头顶飞过了它的身子,落在草丛里“哎哟”了好久。
我一边揉着跌成两瓣的屁股,一边想着我该怎样惩罚它的时候,它慢慢地走了过来,一下一下地舔着我的脚背……
时间到了1984年的9月,我也要上学了。
4
开学第一天,我就被一个高个子男生打了。
因为我上错了厕所,我哪儿知道厕所还分男女啊?我们家就只有一个厕所,如果里面有人,听见脚步声就会咳嗽一声。
我实在憋不住了,犹豫踌躇了好久才冲进去的……
我哭泣的时候想起了它的眼泪。
昨天,父亲像一个金人一样站在霞光里,国槐树旁一堆火,火里烧着一根火钳——当他把它牢牢地捆在国槐树上的时候才从火堆里提起那柄烧红的火钳,我起先和它一样,既不知道火堆里有火钳,也不知道父亲到底要干什么。
父亲让我给它搔痒,我就站在它的身后用小树枝一下一下地挠着它的大腿根部。我有经验,不管是帮猪还是猫还是狗挠痒,它们都会舒服地闭上眼睛躺下来,摊开四肢,放松警惕……
忽然,一股皮肉烧焦的味道钻入了我的鼻孔,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喷嚏,就被它扬起后蹄踢飞了。
我飞了一段距离,才降落,大腿到第二天还疼。
刚才父亲把其中一根烧红了的火钳腿捅进了它的鼻孔,捅穿了两个鼻孔之间的鼻中隔。那股略带烤肉香的焦臭味儿就是这样飘进我的鼻孔的,它也是在那一瞬间受疼才由脑神经下达了飞踢后蹄命令的,我也是在那一瞬间飞起来的,父亲也是在那一瞬间抽出火钳腿然后把早已经准备好的丫字形的树枝插入它的鼻孔的。
它被穿了鼻子。
我跟它一样疼得只掉眼泪。
它惊慌的大眼睛里满是泪水,一颗颗落在地上,我撇了撇嘴巴,没有哭。因为我很好奇,想快点爬过去看“穿牛鼻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它也很快不掉眼泪了,因为母亲为它端来了一盆兑了菜汤的稀饭。
我盯着女厕所上面那个大大的“女”字——那是我生平认识的第一个字——掉了一会儿眼泪,想了一会儿它,去上课去了。
上学并不好玩儿,第一天就挨打。不上学逃学也挨打,母亲用那根柳条狠狠地抽打在我的屁股上,折断成三截,她含着泪发誓,再逃学,一个字,打。
因为我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常常会遇见目光冷峻的狼,所以,八岁才上学。八岁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不自由的。比如说它,还没有成年,就被穿了牛鼻子,牵着走。
深秋的时候,我站在花生地旁,望着它四只蹄子深深地陷入松软的泥土中,弓腰向前,牛轭头深深地嵌入它高高隆起的肩头,母亲在前牵着它的鼻子,鼻孔里淌着血,父亲在后,赤着上身,汗津津的,弯腰扶犁,像一张拉满了的弓。
他们的希望在这泥土里,也在我身上。
如果父亲是那张拉满的弓,大概也是为了射出我这支箭。
它光滑的皮毛水淋淋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脊背上有几道鞭痕,皮毛翻卷,红肿凸起,像几条凶恶的蛇在狰狞地游动。
谁不说咱苦耕田,
吃草干活还挨鞭。
哪是情愿做劳役,
缘于鼻子被人牵……父亲犁地时唱的歌谣,高亢悲凉,声音直冲云霄,我的目光像一支响箭,追随他的声音,射向高天之外的高天……
在这样的歌唱中,我灵魂颤栗,获得抚慰,感慨万千。不知道它是否也如是?
5
它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就像它受伤流脓痊愈了的肩头有了厚厚的茧一样,在秋水河,这些都是生而为牛早晚会有的事儿。
它被叫作“黑将军”的那天,我看见黑滚珠一样的田鼠突然蹿过田野,满山的映山红同时开放。
和其他公牛相比,它更早地获得了过大的荣誉——而很多公牛也许一生也无法获得。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春天来了的时候,它的个头比去年站起来还要高,头顶着两柄锋利的犄角像是枕戈待旦的将士,眼望远方,心在疆场。
战斗发生得很突然,虽然剧烈,却很短暂。
在松林里,我们的一群牛和老铁头的一群牛遭遇了。
这样的遭遇不是一次两次,起初,我们谁都没有在意。
问题出在老头牛群中的几头母牛身上,俊美健壮的它让好几头多情的母牛恋恋不舍,想要跟它耳鬓厮磨。
这是“独角”不许可的。
独角是一头好战的公牛,也因为好战,在前几年和另外一个村子的“牛魔王”大战的时候,失去了一只角,即便如此,它仍旧大败牛魔王,并追了好几个山头。以至于这几年,所有的公牛见了它都躲。
大概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独角出面驱赶它的时候,它突然扭头反击,锋利的犄角刺伤了独角的脖子。
即便如此,独角仍然没有觉得自己遇见了对手。
它蹲踞在一个小山坡上,后蹄刨起的泥土携带着青草和开满小黄花的委陵菊。独角远远地望着它,犹豫着是不是跟随牛群转移到另外的山头。
就在独角犹豫不定的时候,它从小山坡上俯冲下来,粗大的牛蹄甲带起飞扬的泥土,空气中有着被践踏的青草和泥土的气息,高大的松树棵棵直立,继续遮蔽着天空,紧张得忘记了让路。
如果你也如我一样在现场看到过它进攻的气势,一定会认为即便是一棵树,也会胆战心惊地为它让路。
独角毕竟是独角,临战经验相当丰富,只见它头一低迎了过去……
“嘭!”牛角相互撞击的声音……
独角的四只蹄甲一起向后滑去,犁开了青草地,留下了四道深深的沟痕。
接下来就是短兵相接,频繁碰撞。客观地讲,在力量上,独角有优势,但是它毕竟少了一只角。大败牛魔王之后,这些年,独角的权威几乎没有受到过挑战,也没有过什么实质性的交战。和独角相比,它渐渐在战斗中学会了更加熟练地运用它那一对锋利的犄角,眼看着独角处了下风……
我们每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观战,老头的鞭子在空中炸响的时候,差点没把我们的小心脏吓出来。
这一声鞭响也让交战中的两头牛分了神,它趁独角分神之际,奔跑几步,高高地抬起前腿,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了犄角上,向着独角冲撞了过去。
独角被撞得前腿跪地,但是,很快就爬了起来,扭身奔逃。
它没有追击,而是回到第一次进攻的高地,仰头“哞哞”,后蹄刨起许多泥土,像急雨一样纷纷飘落。
老铁头叹息一声,为独角,仿佛也为自己,声调苍凉,现在回想起来,有点英雄暮年的感觉。他说:“独角不去势,未必会输……”
那时我并不明白老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才知道。
那时我只是傻傻地站着,像是望着一位英雄一样望着它,小心脏怦怦乱跳,心里满是骄傲,傻笑着,怯怯地,不敢向它靠近。
过了好久,是它主动走过来,低着头,舔着我的鞋子,然后,又仰起头来舔我的手。
我伸过手揉了揉它头顶心那团白色的毛,跟着伙伴们一起叫它“黑将军”!
6
我迷上打陀螺了。为能玩儿个够,我和同学跑到了离学校不远的粮食收购站。为了晾晒粮食,那里有很大一块水泥地面。
玩得太开心了,中午也不舍得回家吃饭。
我们挥舞着手中的小鞭子,抽打着陀螺,头发汗湿了贴在额头上,汗水滑过鼻尖,也顾不上擦掉。
起初那小小的陀螺只是摇摇晃晃地转动,渐渐地站稳了,发出了“嗡嗡嗡”的轻微声响,仿佛可以永远这样旋转下去……
我们把两个旋转的陀螺用鞭子抽到一起,让它们相撞,或者让它们比试,看谁的陀螺能够一直转下去。
它们真的就这么有耐心地旋转着,谁都不肯先歪一歪身子。
我们也提着鞭子,伸展着胳膊,脑袋上扬,望着一朵白云,像陀螺一样旋转。风过耳,吹落汗滴,天上的白云跟我们一起旋转得晕头转向却又欢呼雀跃。
大概鸟儿在天空中鸣唱,白云随着风飘的快乐,也是这个样子的。
黑将军就是在我最快乐的时候找到我的。父亲刚卸下牛轭锁,还没有来得及擦一把额头和脖子里的汗,它就挣脱了父亲,在看场人的大呼小叫中踩踏着晾晒的粮食,径直走到我的跟前。
它那么威风,却向我低下了头,顾不得喘一口气,连拉屎的时间都不舍得耽搁——黑将军在穿越晾谷场那片分摊均匀的麦子的时候一撅尾巴,把牛粪拉在了晒得铮铮响的谷子上,这也是看场人惊呼鬼叫的原因——它那么那么温柔地垂下头来,一下一下地舔着我的脚背,我的裤管,还有我摊开滴着汗的手掌……
等到头晕目眩的我从旋转飞翔着的白云里飞落地面,一切都晚了。
来公粮收购站交公粮的父亲明白了一切——为了贪玩儿,中午不回家吃饭,并且还玩过了头,下午第一节课应该已经快要下课了……
父亲大吼一声,顾不得把粮食从板车上卸下,提了鞭子就要来抽我。
幸好我跑得快,而父亲恰好又在穿越晾谷场的时候被脚下的麦子滑了个趔趄……
晚上放学还没有到家,姐姐就告诉了我父母都做好了收拾我的准备,就连溺爱我的奶奶也无能为力。
害怕挨父母打,我只好躲在床下面,竟然在担惊受怕中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父母几乎要把整个村子翻个面,很多邻居也打着火把帮忙寻找我,他们甚至都跑到了秋水河,把手电光照在河面上,看上面有没有漂浮着一个小孩……哪怕找到一只鞋子也行啊——哦,连我妈都忘记了,那时家里穷,从四月起,我就不穿鞋了……
多少年过去了,那件事情至今让我的家人津津乐道。
7
一到初夏麦子就骄傲得不行,它们喜欢成片成片地站立着,在风里摇晃着颗粒饱满的头颅,喜欢把风的问候一个个地传递过去,交头接耳,耳鬓厮磨,发出“唰唰唰”的轻响。
人们说,这叫“麦浪”。
六年级要小升初,留在学校学习。我们三年级到五年级共三个年级要去给村委“义务劳动”。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来到深山,割那么几大片麦子。
割麦子的时候我就想,等下午割完麦子后,我要去摘杏子。
山上的麦子熟得迟,刚好赶上摘杏子。同学们都说山上有好多杏子树,每颗杏子都又大又圆又黄又甜……我一边割麦,一边想得满嘴口水,也顾不上麦芒把脖子刺得通红一片。
中午就着山泉水吃了两大块锅贴,这下好了,书包除了两本书之外,也空了,刚好可以装杏子。
下午三四点钟,麦子就割完了。
给村领导做饭的老姜头咋着舌说,可惜了,这么好的麦子全被你们这群小畜生糟蹋了。
回头望望身后的麦田,确实有不少麦子被踩踏或漏割了。可是又能怎样?您知足吧,我们这群小畜生有的比手里的镰刀长不了多少。
那时我读三年级,刚好有两个镰刀长。
我多希望同村里的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去山上寻找杏子,可是,他们都很乖,听老师的话,要快快地回家。
刘伟华还笑着对我说:“太阳落,狼下坡,逮到大人当馍吃,逮着小孩当汤喝……”
我望了望头顶明晃晃的太阳,觉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既无恶鬼,也无饿狼,就提着镰刀背着书包翻山越岭地去寻找杏子去了。
深山老林里的静都是被那些声音给衬的。比如说,突然几只鸟儿拍着翅膀飞过头顶,“布谷布谷”地叫着,由远而近,再渐渐消失;比如,突然,一阵剧烈而快速的敲门声,让人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再细细循声辨过去,是一只啄木鸟的长嘴巴用人们想象不到的频率敲着树干;比如说,一只孵蛋的野锦鸡,在灌木里蹿了好久,才突然“嘎”的一声大叫,飞上了天……
我昂着头,脖子都酸了,还是没有找到杏子树,倒是被这些声音弄得我一惊一乍。突然就想起早些年放牛时候看见的小猪头。奶奶说,那是狼吃剩下的,留着猪头是“孝敬”天老爷的。
常常在茂盛的青草丛中,忽然一群苍蝇“嗡”地飞起,循着臭味,准能找到野狼吃剩的猎物。
这样胡思乱想一阵之后,忽然觉得头皮发麻,后脊梁发冷,不由自主地回头望。
一回头,竟然看到一棵那么大的杏子树,上面果实累累,把树枝都压弯了。我捂着激动得怦怦乱跳的心走到杏树跟前。树下也是一层黄澄澄的杏子——落了一地,几只啄食果实的小鸟儿见我来了,才不慌不忙地跃上枝头。
真甜!我捡了一颗新鲜的杏子尝了尝,酸甜的汁液自口腔沁入了肺腑……
我从树上下来的时候,书包实在装不下了,抽出那几本像奶奶的破布卷儿一样的书,犹豫了一下,扔了。反正就要期末考试了,我都会了。
又犹豫了一下,把那几张考了满分的试卷也扔了。
就又可以多装一些杏子了。我一边捡拾草地上的果实一边想着奶奶会喜欢的,妹妹会喜欢的,姐姐会喜欢的,父母也会喜欢的,嗯,还可以给黑将军尝尝……
蜜蜂从花蕊中飞出来的时候,因为收获太过沉重,常常飞得歪歪斜斜——我像贪心的蜜蜂那样,背着满满一书包杏子,侧着身子,走得歪歪斜斜,却志得意满。
仰头望了望天,才忽然发现光线黯淡了许多,难道太阳要下到山的那一头了吗?
我用提着镰刀的右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大声地唱着歌儿为自己打气,鸟儿“扑啦啦”地扇动着翅膀,在丛林中寻找着自己栖息的那棵树……
翻过两座山,穿出密密匝匝的丛林之后,心里稍微轻松了一点,我看到东山头又大又白的月亮升了起来。
晚风吹过来,我才意识到我唱歌的时候喉咙发紧——不知道是唱歌太久了呢,还是心里的害怕像沉重的暮色一样在一点一点地攥紧我。
我吞了口口水,正准备接着唱不着调的歌谣时,突然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跟随着我——有时,我一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上厕所或走夜路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我。可是,回头望,却什么也没有。
今天,这样的感觉让我的头皮发麻,而且,不敢回头望。可是,越是不敢回头望,越是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我……
或者说,我感觉到了一种让我紧张而恐惧的气息,这样的气息正像夜色一样,一点一点地包裹着我。
它的脚步轻轻巧巧,落地无声,就像霜落在草地上,月光落在水面上……
我大吼一声,唱起了国歌。
我唱得铿锵有力,渐渐地觉得这样的恐惧只是自己吓自己,是一种错觉,可是,当我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心里又“咯噔”了一声,嗓音和声调全变了。
我想,我不能跑,也不能慌张,更不要回头望。
尽管我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回头望,可是,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只瞟了那么一眼,牙齿便开始“咯咯咯”地打颤。
一条比我平时看到的狗要高大很多的东西,和我在同样的月光下。虽然只是匆匆的一瞟,我还是看见了它的尾巴拖垂着。
奶奶说过,狼和狗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狗喜欢摇尾巴,而且,尾巴打卷向上,而狼则拖着尾巴。
8
我意识到自己手里还有一把锋利的镰刀的时候,用力地握了握刀柄,才发现手心里全是汗。
于是,我把镰刀换到了左手,把右手手心里的汗在上衣上蹭干。
吓了一跳,我的上衣竟然全湿了,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
脑门还在“噌噌噌”地冒冷汗。
我的脸因为恐惧像是冻僵了一般死灰,思想却电光火石般燃烧。我想起了奶奶讲过的许多和狼遭遇的故事,她小时候放羊,曾经用手里的鞭子抽打着饿狼,硬是从狼口中救下了一只小羊……
我上下牙床的牙齿“咯咯咯”地碰撞着,胆战心惊地宽慰着自己,我虽然没有鞭子,但是,有刀啊……
就这样,我匆匆忙忙地走了一段路,又下了一个山岗,拐弯的时候,我又偷偷地瞟了一眼身后。
它和我之间的距离更近了。
如果它再不下决心进攻我,那么,再翻过一个山岗,就到了我们经常放牛的松林了,那里离家已经很近了。
很显然,它也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我发现,它这时已经不想隐蔽自己了,有时还故意弄出一些声响,是在试探我的反应吗?
我腿一软,差点歪倒在地,杏子从书包里漏掉了好几颗,也顾不得捡了。嗓子干得不行,想大声呼救都发不出声来。
忽然,月光下一个庞然大物正迎面向着我走来……
这样的大块头,天啦,难道还有黑熊?
可是,听奶奶说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遇见过熊瞎子了啊……
前是熊,后是狼,我死定了。
我愣了愣,不知道该继续向前还是转身退后。
忽然,我想起来,可以上树啊!
我望了望身旁的这棵松树,就算我发挥正常,能以最快的速度爬到树上去,估计我一动念刚走到树下,还没有开始爬,无论是熊,还是狼,它们都能在我开始爬树之前把我拉下来……
我举了举镰刀,把“咯咯”响的牙齿咬紧,回转身去,那条狼已经不见了,而那个庞然大物在月色下却越来越清晰。
是我的黑将军啊!
它走到我的跟前,低下头,轻轻地舔着我的裤脚,我举起汗津津的手,让它舔我的手。
黑将军拖着一截绳子,是父亲没有拴紧呢,还是它挣脱了?
我搂着黑将军粗壮紧实的脖子,在月光下默默地哭着。
哭了一会儿,我又回头望,只是一片白茫茫的月光,狼大概是被黑将军吓跑了。
我就这样抱着黑将军的脖子,簇拥着它,在月光下往家的方向走,那里应该有一片灯火人家。
可是,一拐弯,我愣住了,那个高高的山岗上,蹲坐着的不正是刚刚消失在月光下的狼吗?
它挡住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黑将军喷着响鼻,低下头,用前蹄刨着地面,飞溅起来的泥土石子儿,击打在松树的枝干上,发出“咚咚咚”的轻响。
那头狼,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我和黑将军都有点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过去还是再等等呢?
那头狼,转了几圈,并没有进攻的意思,竟然像一条狗一样,卧了下来,把头搁在两爪之间的地面上。
月光透过松林的枝杈影影绰绰地落在它的身上。
忽然,我听见了“噼啪”一声响,好熟悉的声音啊。
听声音,是在我的身后。
我扭过头去,只见另有一头狼,低着头,前肢半跪在地上,也被这声音吓了一跳,正偏了偏头,竖起耳朵,一动不动。
它离我只有两三米的距离,借着月光,我看得如此清晰。它灰色的泛着油光的皮毛,缺了一半的左耳,开到耳边的黑色嘴巴和嘴巴里露出的森森白牙……
卧在我们前面挡住我们的去路的那头狼,双爪按地,半蹲了起来,两只耳朵完好无损。
又是一声“噼啪”响,比过年时候最喜欢玩儿的二踢脚还要响。
那个骑牛的老铁头出现了。
他骑在那头老牛身上,身后还跟了一头小牛犊——估计这是从牛群里落单走失了的小牛犊——老头喜欢放牛的时候喝酒,往往喝多了就睡着了,睡着了,就会落下一两头牛在山上。
那天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会突然在我身后出现。
老头长长的鞭子在空中再次炸响,我看见身前身后的两头狼都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松林中,几乎是一眨眼之间。
随着它们的消失,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我的那种恐怖氛围一下子就没有了。
月朗风清。
只是老头骑着的那头老牛被两头狼吓着了,发力狂奔,把老头从牛背上掀了下来。
我去扶他,他不让,自己一瘸一拐地追赶着在不远处等着他的那头老牛。
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每次都要骑牛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他有腿疾,是个瘸子。
9
在学校里做题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黑将军,想起它来,仿佛就有了力量。那一个个难题,就像一头头妄想挑战它不断长大的小公牛,它们一个个地红着眼,向着黑将军发起进攻,然后,再一个个地败在黑将军一双锋利的犄角之下——那些仿佛永远无法解答的难题,也败在我的笔尖之下。
我因为把自己想象成黑将军而有了魔力,笔尖也像一只鸟儿灵巧的嘴巴,在纸面上“剥啄”地响着,解开那些看似千千结的难题。
那时,我已经住校了,进入总也吃不饱饭却常常陷入孤独和迷惘的青春期。我望着窗外自由飞翔的鸟儿,往往是夏天快要到了,还不知道换下冬天的厚衣服;往往是飘起了雪花,才知道没有可以御寒的冬衣。
面对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我常常拱一拱肩,仿佛身后有着一张无形的犁铧,像黑将军那样,我让犁铧深深插入泥土,让泥土像风吹水浪一样翻滚在身后。
我还常常想起,那次我逃课玩陀螺的时候,父亲赤着身子,弓着腰,把一麻袋两百斤重的小麦扛在肩上,晃晃悠悠地走过用两块窄木板搭就的接近五米高的浮桥——浮桥的一端在平地,一端是高高耸起的粮仓——父亲剃着光头,脑门上都是汗,全身的汗水使他看起来仿佛是在阳光下镀了金身的弥勒,只是他没有弥勒的笑容,而是咬着牙,鼓着腮帮,肩负着命运赐给他的幸福和苦痛。
我终于找了个机会从书山题海中回到家,看到黑将军的时候,我发现它愣了愣,在见到我的一瞬间眼睛里有了光。
它像往常一样,低着头,缓缓地走过来,舔我的脚背,舔我的裤脚,舔我的手……
只是,我发现它走路的样子很怪。很快,我就发现了原因。
它被去势了。
父亲说,为了省钱,就请邻村里的老铁头做的手术,很不成功,有点感染了。
我看见黑将军后腿之间肿大了两倍的牛睾丸,淅沥着血水,沾满了苍蝇,心里一阵排江倒海地翻腾,想吐,没有吐出来,全变成了心绞痛。跌坐在地上,满脸泪水地望着黑将军,它一下一下地舔着我的手掌。
我发现它初见我时眼睛里的光,化成了泪水淌了下来——眼睛黯淡了不少。
它长长的睫毛像鸟儿展开的翅膀那样美丽,它眨了眨眼睛,又流出一行泪水,眼睛里的光更少了一些。
泪水在它的脸上留下了两道湿痕,它的皮毛竟然有些皱缩翻卷,脊背上一道道的鞭痕,结成了硬痂,上面寸草不生。
这是我第三次看见黑将军流泪,后来,这泪水我全还给了它,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长期在外地求学,很少回家,黑将军已经渐渐不认识我了,不记得伴随着它一起成长的那个男孩了。而那个在月光下一步三回头的小牛犊,在松林中挑战独角一战成名的黑将军,那头还能感应到小主人危难以身护主与狼对峙的黑将军,也日渐老去……
那是高二的寒假,长期吃不饱饭的我因为一顿美餐吃得大汗淋漓,只是,家里人的气氛不对,大家都有些沉默,仿佛对我掩饰着什么。
吃完饭后,我问,这是什么肉,怎么这样好吃?
父母却只顾左右而言他,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去牛圈里找黑将军。
牛圈里空空的,但我能闻见它留下的气息。
“黑将军是邻村的老铁头杀的,”父亲说,“它没有遭罪,它活着才是遭罪呢,肉是老铁头送过来的……”
我蹲在牛圈门口蹲了好久,我以为我会哭,但是,却一滴眼泪也没有。闭着眼睛,仿佛黑将军来了,嘴巴一张,想要呼唤黑将军的名字,却一口酸水呕了出来,接下来,就是呕吐,一边呕吐,一边流眼泪。
吐完之后,整个人像是大病一场,虚脱了,正准备站起来的时候,它真的来了,还是那样低着头,舔着我的脚背,我的裤脚……
我伸出手,好让它酱紫色的舌头舔我的手心,没有动静,睁开眼睛,什么也没有,眼前是一大片绿油油的冬麦,和一大块黑将军翻过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