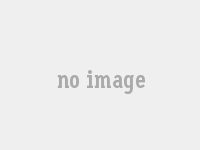华盛顿总统辞职演讲(华盛顿的成长故事华盛顿放弃连任-卸甲归田种夕阳)
在1790年代上半叶,美国政治生活中最接近不证自明的真理的人物,只有乔治·华盛顿。

作为那个时代的传奇,美国人自1776年(也就是说在国家尚未成立之时)就将他视为“国父”了。在他1789年担任总统之时(让其他任何人担任总统在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关于华盛顿声望的各种神话已经如雕像上的常春藤一般疯狂生长起来,华盛顿本人完全被笼罩在一种无所不能的光环之下,使区分他作为凡人所拥有的才能和他的那些英雄主义成就变得几乎不可能。
在那些难以置信的故事中,某些恰巧是真实的。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1775年在匹兹堡外对法国军队的进攻以失败告终,年轻的华盛顿与丹尼尔·布恩一道将幸存者召集起来,尽管这个过程中他先后从两匹马上跌落下来,外套上有多处弹孔,裤子上也多处被擦破。1781年在约克镇,在一次炮火攻击的枪林弹雨之中,他站在一堵矮墙上达15分钟之久,完全不理会那些试图拉他下来的助手,直到他完全探清战场形势为止。当华盛顿开口谈论国家命运之时,人们洗耳恭听。
如果这个新生国家有一座奥林匹斯山的话,所有那些次要的神都只能远远站在山坡下。唯一能够和华盛顿争夺最高地位的只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是在1790年去世之前,富兰克林本人已经承认了华盛顿的至高地位。富兰克林以其典型的姿态,将自己的手杖遗赠给了华盛顿,好像是要帮助这位将军迈向不朽之路一样。“若说这是根权杖的话,”富兰克林说道,“他应当得到它,而且完全与之相称。”
在1790年代的美国,华盛顿的形象无处不在,在绘画中、报纸中、纪念盒中,在硬币上、银器上、碟子上、家庭小摆设上。人们对他的亲密情感似乎会永存下去。他的指挥官身份已经成了独立战争年代每一个重大事件的核心特征:1775~1783年大陆军的关键人物、1787年制宪会议主席,以及自1789年以来担任这个羽翼未丰的联邦政府的第一任最高行政首脑。他让独立战争时代的狂想曲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可感知的现实,是美国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华盛顿是引力核心,防止美国独立战争步入混乱轨道;他是稳定的中心,围绕在他的周围,独立战争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正如当时一句流行的祝酒词,他是“将所有的心灵团结起来的人”。他是宙斯、摩西和辛辛纳图斯三者合一的美国伟人。
告别信
1796年9月19日,一篇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文章出现在了费城的重要报纸《美国广告者日报》的内版上。这份声明非常简单,体现出作者精心设计的平易措辞。它是这样开始的:“朋友们,公民们:重新选举一个公民来主持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经为期不远了……我认为此时将我的决定告知诸位是恰当的,尤其是考虑到这将有助于公众意见的更明确表达。这个决定就是我将不再接受进入候选人名单。”这份声明以未加任何头衔的签名结束,表现出作者的自谦姿态——“乔治·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
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国内所有主要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尽管只有《新罕布什尔快报》给它加上了将永载史册的标题——“华盛顿的告别演说”。
当时人们几乎马上就开始对文章内容展开了辩论,一个生动而愚蠢的论辩出现了:它到底是华盛顿写的,还是汉密尔顿写的。在之后更长的时间里,这份告别演说获得了超越一切的不凡地位,与《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一道成为对美国必须永久遵循的原则的基本宣言,庄严的语调也使它成为充满陈腐智慧的政治场景中的永久试金石。19世纪末,国会让在华盛顿诞辰日朗读这份演说成为一项强制性仪式。同时,几代历史学家在美国外交研究者的带领下,将解释这份告别演说变成了一种专门研究,并对蕴含其中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和美国两党政治做了无数评论。
但在当时,这些矫揉造作的姿态或解释根本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存在意义的话)。真正有意义的而且大多数读者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乔治·华盛顿要退休了。当然,人们也马上领悟到这个决定在宪法上的意义: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自动放弃了总统职位,确立了一个直到1940年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破的先例。(这个先例于1951年被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重新确认。)但是,即使是这个在确立总统轮换制的共和原则上发挥关键作用的里程碑式先例,相比于另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和心理认知,还是显得黯然失色。
二十年来,在独立战争和共和政府实践的整个期间,华盛顿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舵手。现在他正航向自己的迟暮之年。他确立的这个先例现在看来可能是令人振奋的,可是在当时,最为耀眼和最令人难过的现实是,没有华盛顿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事实本身是前所未有的。这份告别演说,正如几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显得有点奇怪,因为它并不是一份真正的告别演说,它从来就不是以口头演说的形式发布的。因此,最恰当的说法是一封“告别信”,因为它在形式和语调上都像是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告诉他们现在他们需要独立前行了。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表达了华盛顿“对内团结、对外独立”的政策理念。与《独立宣言》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一道成为对美国永久遵循的原则的基本宣言。
享受“光荣的孤立感”内幕人士在六个月以前就觉察到这一天快要到来了。1796年2月时,华盛顿曾就起草某种形式的告别声明找过汉密尔顿。不久之后,政府内部的消息网络嗅到了气味。当月末,詹姆斯·麦迪逊写信给正在巴黎的詹姆斯·门罗:“非常肯定的是,华盛顿总统不会在此次任期结束之后继续担任总统。”
发表告别演说前夕,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领袖菲舍·艾姆斯预言,华盛顿即将发表的声明将成为“开启党派竞争的信号”,但是实际上这种竞赛已经在此前的春季和夏季非正式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例如,在5月,麦迪逊就猜测(事实证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竞选,“杰斐逊可能是一方,亚当斯明显是另一方”。仲夏之时,华盛顿本人已经开始向朋友们透露自己任期结束之时离开政府的强烈愿望,“自此之后,天底下没有什么我能预见到的东西能够再次将我从私人生活中拉回来了”。实际上,在整个第二任期期间,他就已经做出种种暗示,说自己“已经到了人生转折期”,过于年迈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并多次重复他的口头禅:他渴望在弗农山庄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享受“光荣的孤立感”。
他是认真的吗?对劳累的政治生活的哀叹和对退隐田园的大力赞美,已经成了独立战争那一代(特别是弗吉尼亚王朝)领导人惯常的甚至是程式化的姿态。每个人都知道西塞罗和维吉尔描述的、以辛辛纳图斯为代表的晚年隐居经典模式。宣布自己要脱离喧闹的政治生活,回到原野或者农场的自然节奏之中,这几乎成了一种修辞惯例。
如果说华盛顿的退休之歌以“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为特征,那么杰斐逊的告别则以偶像化的“我的家庭、我的农场和我的书籍”为特征。这种特征后来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如西塞罗般充满抱负的约翰·亚当斯宣称,弗吉尼亚人已经用尽了西塞罗式的行为表现。“看起来让自己变得伟大的方式就是退休,”他在1796年给阿比盖尔的信中这样写道,“政治植物是如何在阴影之中生长起来的,这真是令人感到惊奇。”
华盛顿甚至在1789年就任总统之前就威胁称自己要退休了,而且在1792年第二次当选之前也重复着同样的威胁。尽管在这些情况下华盛顿都是真诚的,但他对体面退休的偏好总是被另一种更公开的美德压倒,这种美德本身被其他政界人士的一致判断强化了:华盛顿,也只有华盛顿,才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在1796年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年龄是原因之一答案很简单:年龄。在华盛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强健一直都是他的无价财富。身高接近6英尺4英寸、体重略超200磅的他,比同时代男性整整高出了一个头。(约翰·亚当斯称,华盛顿每次都被选为国家行动领导人的原因,就在于他总是屋子里面个子最高的。)若对他的身体特征进行客观描述的话,他几乎就像一个丑陋的畸形人:脸上布满麻点、龋齿严重、眼窝深陷、鼻子过大、臀部肥厚、手脚大得惊人。然而,当这些东西被放在一起并运动起来时,整个形象却放射出庄严的光辉。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言,他的身体不只是占据空间而已,似乎还将周围的空间重新组织了一遍。他不仅以其庞大的身躯在屋内占据了主导,而且几乎就是一种电磁式存在。“他的举止是如此庄重和威武,”本杰明·拉什说道,“以至于欧洲任何一个国王站在他身边,都好像是他的男侍从。”
华盛顿似乎能让战斗中的子弹和炮弹碎片绕道飞行;他曾经将石头扔过了舍南多瓦山谷中高达215英尺的天然桥;他被普遍认为是弗吉尼亚最好的骑手,在大多数猎狐行动中都居于领导地位。除此之外,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拥有似乎免疫于任何疾病或者伤害的体格。其他士兵在游过浮冰拥塞的河流之后,都会出现冻疮。其他政治家倒在路旁,因为他们缺乏应对政治压力的非凡毅力。华盛顿不曾受过此类病痛之苦。亚当斯说,华盛顿拥有“沉默寡言的天赋”,指的是他有一种化沉默为雄辩的本能。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医疗记录也呈现出一种雄辩式的空白。
他那钢铁般体格中的裂缝,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他在1787年制宪会议开始之前病倒了,差点错过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接着在1790年,就任总统之后不久,他染上了流感,当时这种病正在纽约州肆虐,差点因为肺部感染而死去。杰斐逊关于华盛顿的言论是充满矛盾、极不可靠的,但正是他记录了华盛顿身体状况开始下滑的时刻:“他那种不同寻常的坚定语调,已经开始松弛了;对工作的倦怠,对宁静的渴望,还有那种让其他人替他采取行动甚至思考的意愿,已经悄悄侵袭了他的心灵。”
1794年,当他骑着马在新首都地区游荡时,他的背部被严重扭伤了。骑马打猎的生涯结束了,美国最佳骑手的历史盛名也随之烟消云散,华盛顿再也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安坐在马鞍之上。年过花甲之后,他结实的肌肉开始松弛;笔直的站姿也开始向前倾斜,就好像他总是被风推着似的;他的精力也在漫长的一天结束之时开始衰退枯萎。敌对的报纸含沙射影地谈到了华盛顿的老态。即使副总统约翰·亚当斯也承认,华盛顿在某些公共仪式上显得迷离茫然,完全需要照稿宣读了,就好像演员不是在表演,而只是在念台词一样。
或许,年龄本身就足以让华盛顿义无反顾地回到弗农山庄。毫无疑问,如果说有人应当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度晚年,那么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或许,正是这种奇特的直觉让他总是能够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间的差别,让他从骨子里认识到,再担任一届总统意味着他将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开了让生物规律结束任期的命运,也避免了开创带有终身君主制意味的先例。对他两届总统任期先例的过度沉迷,使我们忽略了他自动退休所确立的另一项更为根本的原则,即政府职位应当超越任职者的寿命,美国总统制与欧洲君主制有着根本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用完可抛的。
被反对派言论伤害然而,年龄和身体疲惫仅仅是整个答案的一部分。或许最简单明了的说法是,华盛顿离职不仅是因为他听到了死神的耳语,还因为他受到了伤害。他未曾被独立战争中的子弹伤害,却在第二任期内被反对派言论伤害了。例如,在他的告别演说发表之后,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的《曙光报》(Aurora)上出现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那位总是惹事的托马斯·潘恩庆祝华盛顿的离去,实际上也是祷告他立即死去,接着又预言“整个世界将为决定您到底是个叛国者还是一个骗子,您到底是放弃了好原则还是从未坚持过什么好原则而感到为难”。
还有些文章完全是荒谬的,也出现在《曙光报》上。它们称最近获得的大不列颠战时文件表明,华盛顿是一个秘密的叛国者,在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与英军狼狈为奸之前,他都一直打算出卖美国人的事业。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华盛顿的批评者属于少数派,其支持者远远多于这些人。例如,对潘恩的反驳立即纷纷出现了,这些反驳将潘恩说成“那个著名的酒鬼和异端”,他诋毁华盛顿声誉的行为“就好像一只爬虫将自己的毒液喷向大西洋或将它那肮脏的涎水喷向太阳一样徒劳无益”。事实上,潘恩当时那已频遭质疑的声誉,再也没有从这次事件中恢复过来。在独立战争年代,攻击华盛顿是政治自杀最快捷的方式。
尽管如此,这类攻击仍然在华盛顿的第二个任期屡见不鲜。虽然华盛顿总是摆出那种惯常的、不为所动的姿态,但他还是被这些攻击深深地伤害了。“然而这些攻击,这些不公正且令人不快的攻击,将不会使我的行为有任何变化,而且它们也不会对我的心灵产成丝毫影响。”尽管华盛顿不像亚当斯或者杰斐逊那样,读了数量惊人的著作,但他绝对是个酷爱读报纸的人。(他在弗农山庄订阅了10份报纸。)他那种完全不理会的姿态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因此,狠毒尽情地投出它的飞镖,”他解释道,“但任何世俗的力量都无法剥夺我因清楚知道自己从未蓄意犯下任何错误而得到的安慰,不论我曾出于其他原因而犯下的错误是多么不可计数。”这种超然却大胆的自我辩护,似乎是在以间接的方式确认,批评者已经触动了他的神经。
对华盛顿的主要指控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准国王。“我们给了他一个国王才能享有的权力和特权,”纽约一家报纸这样写道,“他就像国王一样主持早朝,他像国王一样接受生日祝福,他像国王一样雇用他的旧敌,他像国王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像国王一样把其他人也封闭起来,他像国王一样接受顾问们的意见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这其中几项指控完全是别出心裁的错误指控,而这些指控中的真实成分就是华盛顿成为权力化身的事实。他曾乘坐由六匹淡黄色的马拉着的华丽马车巡游费城;骑马时,他的白色种马身上常搭着美洲豹皮、安着金边马鞍;他曾在在公共典礼上接受桂冠,如加冕礼一般,等等。他对以上这些事实没有丝毫的后悔之意。而且,当纽约市民寻找另一尊雕像来替代被推翻的乔治三世的雕像时,他们选择了华盛顿的木制雕像,这让某些批评者把他称作“乔治四世”。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语言问题。以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共和国行政首脑,因此除了那些欧洲宫廷和国王建立起来的口头传统之外,就没有其他词汇来描述这样一种新事物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个性问题。华盛顿骨子里是一个倔强而拘谨的人,他总是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姿态,而且习得无可匹敌的维持距离感的技巧。这的确强化了他的威严,但是有点过头,这位威严的人几乎成了“国王陛下”。
独立战争的核心遗产除了外表、语言和个性之外,更大的问题其实深嵌在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的要求很快就显出利弊。捍卫独立战争成果及其遗产需要一位超群出众的领袖,他能够将全国政府的能量集中在“非凡人格”之中。华盛顿投身于这项事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变成了政治规则的受益者,最终被赋予了“共和国王”的角色;他所代表的国家权威,比任何诸如国会这样的集体机构可能传达的权威都要更有力、更直观。
然而,独立战争的核心遗产恰恰包含着对君主制的痛恨和对任何集中化政治权威的怀疑。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主要信条是——杰斐逊将它写进了《独立宣言》——所有国王,而不仅仅是乔治三世,本质上都是邪恶的。因此,共和国王这种概念本身就是对“1776年精神”的违背,就是一种词语上的矛盾。华盛顿的总统任期恰恰就陷入了这种矛盾之中。他生活在早期美利坚合众国的巨大矛盾之中:政治上对这个新生国家至关重要的东西,却在意识形态上与这个国家想要代表的东西相悖。他如此干练地履行了自己作为“非凡人格”的职责,以至于似乎违抗了共和传统本身;他如此成功地成为国家权威的化身,以至于任何对政府政策的攻击似乎都是对他个人的攻击。
这是把握华盛顿在1796年离开公职的动机的核心背景。他实际上是在通过主动辞职宣称,自己内心最忠诚的信念和那些批评者一样,都是共和的。他实际上是在向他们做出回答,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决定性的行动。而且,这也是理解他的告别演说的适当起点。华盛顿实际上是在以美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仁慈君主的身份发表最后声明。不论告别演说经过两个世纪的不断解释已经具备了何种意味,华盛顿希望用它告诉国人,如何在没有他、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团结和意志。